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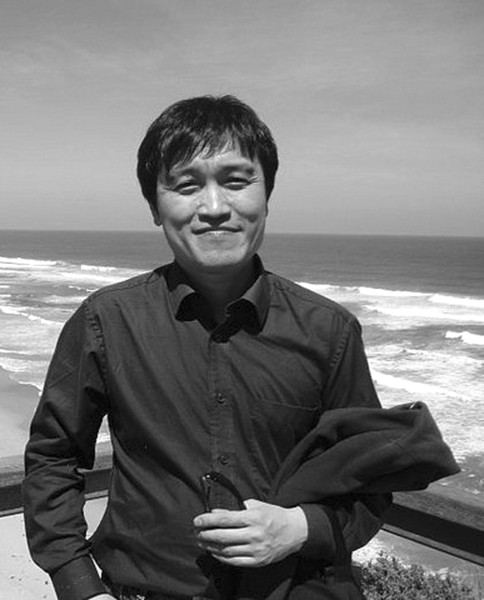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对有些人来讲确实是这样。但对另一些人,这个秋天却显得平平常常,甚至恰好相反。
丰收感最强烈的应该是来自中国电力集团山西娘子关发电厂的科幻作家刘慈欣。他的小说《三体》第一部的英文版被美国最有经验的科幻出版公司TOR正式发行美国版,而翻译者是近年来在美国颇受好评的华裔科幻作家刘宇昆。
刘慈欣没有应邀去纽约进行发售活动。但在国内,他接受了大大小小的专访,畅谈了自己对科幻小说、科幻电影和中国科幻走向世界的感受。站在山巅的刘慈欣收起自己的笑容,做出深思状的照片于是出现在大大小小的报纸杂志的封面或题头之上。
讲述刘慈欣的故事,离不开传统的艰辛中成长的主题。身处偏远所在的他,从小就是一个科幻迷:枯燥的日常生活,亟待拯救的普通人的生命循环。在一次中央电视台的读书采访中刘慈欣承认,在高考报名的当日,他读到了英国作家亚瑟·克拉克的小说《2001:太空漫游》。那一天,整个世界在他眼前彻底改变了模样。创作科幻小说成了他最大的梦想。而这个梦想的实现,走过了蛰伏的10年和尝试的10年才接近了收获的季节。没完没了的修改,再投稿仍然被拒,侥幸地成功发表却毫无读者反响……
9月20日,四川《科幻世界》杂志和上海初创未来公司为了跟世界华人科幻协会争夺眼球,提前召开“未来大会”,同时颁发银河奖。
《科幻世界》原名《科学文艺》,它1979年创刊。在创刊的前10年中,这个杂志经历了繁荣、跌落,从饱受期待到饱受争议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典型历程。
在老一辈《科幻世界》主编人杨潇和谭楷的眼中,《科幻世界》的从死到活,差不多就是他们摸索中国改革开放的命运、在艰苦的时代中仍然跟作者和读者披肝沥胆共同奋斗的成长的奋斗史。刊物低谷的时候,发行只有几千份。所有编辑部的员工不得不为了生存投入编辑教辅读物。等把一捆捆的读物从印刷厂取回并送到学校,你才有空余的精力回到科幻作品的编辑上来。
在尝试过多次人工呼吸和濒死拯救之后,他们等到了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终于,从死亡中归来的体验变得神圣而遥远。随着杂志逐渐走向真正的成长,它开始在中国读者眼中成为一块圣洁的招牌,期刊不但从数量和质量上大规模扩充,甚至把所有成功的科幻作者都保护到自己的麾下。韩松、王晋康、星河、何夕还有更多的新生代与后新生代传人,前仆后继地出现在这个刊物的封面作品名单之中。
任何一个对科幻这个行业稍微有点儿研究的读者都逐渐会发现,在这个海域中露出水面的所有冰山,在亮丽且能反射出灿烂月光的水面部分之下,都有着艰难且不可告人的痛苦的奋斗史。这是一个不可告人却尽为人知的公开的秘密。你要走向巅峰,先要堕入低谷。
此时此刻,还有多少人在低谷中游荡着寻找出路?
跟刘慈欣差不多同样出生于60年代的熊伟,对许多科幻人来讲完全是一个没有听说过的名字。
熊伟中等身材,面色微黑,戴着深色的眼镜,讲起话来既有建筑业人常见的那种豪爽直率,也有知识分子式的包容退让。熊伟可能是当今最重要的几个对科幻电影发展起到强烈推进作用的人中的一个。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中,他至少举办了三次科幻电影发展专业研讨会,又跟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的沙锦飞、DMG娱乐的徐卫兵、春光公司的楚戈等几个人共同发起组建了中国第一个科幻电影促进委员会,将六大民营电影公司中的至少三家的老总请进协会支持。现在,他为这个领域中第一套多季集科幻网络电影做了前期准备。
“我原来是做建筑规划设计,90年代从川美的几个朋友那里看到了《科幻世界》这个杂志,觉得很有意思。2008年,金融危机后,各行各业都在谋求改变时,三聚氰胺等一些事件触动了我,觉得这个国家应该在科学技术标准等方面做太多的工作。2009年有幸我来到北京景藏健康文化公司,在一次会议上听到了有关中国文明到底有5000年还是8000年的演讲故事,我开始对这些超出现有知识的东西越来越感兴趣。这之后,我在中影华纳横店工作的朋友的帮助下,开始学习剧本写作。我外公是电影《抓壮丁》中的导演陈戈,2010年刚好是他去世30周年,为了纪念他,我写了第一个科幻剧本‘银河文明-守护者’。剧本给影视界朋友看的时候大家有的说好,有的说欠火候。这是坚定信念的开始,2013年我决定做些微科幻电影。有朋友给几十万定金,我也有厉害的导演朋友和搞科幻美术的师兄。但搞来搞去,发现不是这里就是那里掉链子,项目播放出口也很难洽商收益。思考感觉可能是我没找到高手的缘故,但发现实际上这个领域高手本来就不容易。对科幻电影来说关键在人,编剧、导演、美术、特效后期等关键人才,有了这些,才能得到投资青睐。现在,为了实现科幻电影这个梦想,我依靠本行工作收益不断地在做项目前期投入。我自己一些很得意的商业投资项目都放下了。几年下来,虽然已经消耗投入了上百万,我还在继续。只不过我现在变得有些缩手缩脚了。毕竟钱不多!”熊伟对我说。
跟熊伟差不多正在潜心推动科幻电影发展的人我还见过很多。这其中最大的一群,是来自80后的主力军团。杨俊杰、乔飞、王语堂、鹿秉书、李恩颖也许能成为这些人的代表。这群人多数在电影学院学习过或进修过。儿童时代的科幻想象力,导致他们义无反顾地投身科幻电影事业。杨俊杰投拍了柳文杨的小说《一日囚》,这个片子参加了湖南卫视《我要拍电影》栏目,还拿到了全国50强。他拍摄的100分钟长片《走马灯》在南京工人影城放映,最后还送去了64届戛纳电影节。
比杨俊杰更成功的是乔飞。他拍摄的《冬眠》是我看过的第一部拍摄得具有大片感的中国科幻微电影。科幻电影评论家西夏特别推崇这个短片,还说服华谊兄弟公司替它做了首映式。据说该片后来在各地参加了多个电影展映,并获得几十个奖励。乔飞也因此被张艺谋的某个新片剧组邀请。他说《冬眠》账单花费在40万左右,不在账单上的,无法计算。
鹿秉书跟李恩颖于2012年开始合作拍摄了《火星之眼》。整个电影投入了300万了。到今年年底才能出第一个预告片。他们说《火星之眼》类似一个系列电影的chapter one,后面还有全新内容。
我已经讲了太多致力于科幻电影的青年在这个秋天的投入和工作。我发现这些人多数没有从电影的制作上获得任何经济补偿,但他们所从事的一切,对未来的科幻电影发展却至关重要。正是他们积累起了无数在制片、导演、表演、摄影、美工等方面的微小经验,也正是他们把一系列散漫分布在各个行业中的人吸纳到科幻电影的事业之中,这一长期工程可能比他们的电影本身更具有价值。
同样是在这个秋天,科幻行业还有另一些被忽视的存在。这就是那些正在为从事科幻研究和探索、想要发现这一文学艺术领域内部深层结构的人。
任何一个熟悉中国科幻史的人都知道,从1902年梁启超发起新小说运动和1903年鲁迅翻译凡尔纳小说《月界旅行》开始的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一直被现实政治或社会变革反复中断。多年来,破解这一发展困局的钥匙,就是要深度分析这种外来文类的内核所在。
以科幻研究为主题撰写博士论文的学子王卫英,一方面要准备在初创未来大会上的发言,一方面要筹备即将召开的王晋康作品研讨会。此外,她还在策划一些新的科幻图书的选题。
王卫英在兰州大学文学院博士毕业,在武汉大学文学院进行过博士后研究。在她看来,中国科幻文学跟主流文学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切合。她的论文讨论了科幻文学的美学特征。毕业后的王卫英先是在中国科普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她跟前任副所长共同发起并参与了百年中国科幻精品赏析的编辑和撰写,这项计划把各个时期的重要作品进行了深度梳理,同时也汇集了许多不同行业的科幻研究人才。但就是这样的研究也会引发一些非议。科幻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已经毕业的困惑无法跟正在读书或撰写论文者的困惑相互比较。那是另一些必须攀爬的障碍。高寒凝、贾立元和梁清散是这些人中的两个。
高寒凝是小学2年级读过刘兴诗《失踪的航线》之后爱上科幻的。在安徽大学书摊购买《科幻世界》的时候,她遇到了两个正要创办科幻协会的姑娘,三个人一见如故,立刻跑去注册新的协会。高寒凝写过科幻小说,有许多自然的创作冲动,但她更多地还是把精力放在了文学研究上。在北京师范大学读硕士期间,她获得导师的理解把论文的焦点指向了新中国早期的科幻小说,并在这个领域作出了第一个全面的梳理。在一次落选之后,她成功地考上了北京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报到的兴奋还没消失,她开始了新的担心,导师能让她把论文的目标指向自己喜爱的科幻吗?
据我所知,在高校跟导师之间协调,期望以科幻文学作为论文内容的人还不在少数。有的人得到了同意,有的人被驳回。先被驳回后得到同意的人也有。贾立元就是其中的一个。
贾立元笔名飞氘,在科幻领域已经是成名作家。从北师大环境工程系本科毕业后进入文学院科幻方向做硕士研究,以优异成绩毕业之后,他进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师从格非教授从事博士研究。起初,导师对他博士论文继续以科幻为选题持有疑虑。“这个领域比较偏门,能否做一个和科幻无关的题目?跳出自己熟悉的领域,也许可以得到更扎实的学术研究训练。”在经历了痛苦的纠结和一些尝试之后,他再次把方向转回科幻,导师也最终认可了他选择的晚清科幻这一研究主题。但是,在难于寻找的报纸杂志中寻觅作品和相关文献的工作是如此的艰难,何时才能完成这项工作?
相比高寒凝和贾立元这种正在体制内进行科幻研究的人来说,梁清散的工作就更加艰难。梁清散从小喜欢《科幻世界》和美剧《超人》及日本科幻动漫,还读过《物理世界奇遇记》。1999年,他高考正赶上《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这个被科幻世界“押中”的作文题。毕业之后设计院无聊的工作让他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在创作了一系列以古琴演奏家为内容的传记之后,他彻底辞去工作转而开始科幻创作和研究。现在,已经成为最世文化签约作家的梁清散还坚持着自己的业余科研。他根据武田雅哉和林健群、李广益等所做的基础书单编制的《晚清科幻书目》获得了大众的好评,现在他继续在新时期早期科幻方面进行着努力。
“对我们这些体制外的人来讲,找资料找不到是最大的问题。许多图书馆都必须副教授、博士学位或者介绍信。我则只好看管理员今天心情是不是好。心情好,我就能进去看一两本。”
当然,这些年发展中国科幻研究的成果并非仅止于此。一个有价值的共识是,这个文类在过去100多年间走过了西方200年的道路,这其中经历了数次高潮,也有过多次低落。
一般来讲,凡是这个国家想要崛起、雄心勃勃地面对未来的时候,科幻作品便会迎来一个新的高潮,而一旦社会发展进入攻坚期或动乱期,便会遭遇质疑甚至驱除。面对一个新的当口,中国科幻的发展机遇已经出现在所有人面前。但这一次的发展,跟过去的数次以从上到下方式引导的“向科学进军”发展有所不同,市场经济将主导整个进程。
在小马奔腾电影公司担任剧本总监的严蓬和独立制片人王语堂都认为,科幻片在类型片领地必须也必定占有一席之地。这在蓬勃发展起来的中国电影行业中已经成为了一个特别的突破口。更多这个领域的从业者也指出,当前面对电影行业的崛起,新颖的剧作不够、合格的编剧不够、合格的科幻制片人也不够。《科幻世界》主编姚海军说,当前作者的青黄不接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他在一次跟笔者的通话中特别说,当前一些成名作者都纷纷被各个公司签约,发表作品的领地被严格限制,而新作者缺乏生活,甚至文字功力也不够。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个科幻行业的发展和进步。
对此我深有感触。近年来,我几乎担当了所有国内各种科幻大赛的评委或电影展的评委,从看到的作品,确实发现特别有创意的作品太少。人们津津乐道的,都还是过去的那些东西,甚至创作的手法也没有逃出已有的“《科幻世界》体”。
重庆大学教师、从海外归来的李广益在一次邀请我讲演时谈到,中国当前的发展,特别是“一路一带”的建设,将给整个世界带去翻天覆地的未来。但这样的故事,在科幻作品中几乎没有见过。而陈楸帆则在他反复强调的“科幻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中,给科幻文学提出了严肃的书写当代的任务。
无独有偶,在第二次日本国际科幻大会上,33位全球作家共同撰写了一个公报,其中指出,科幻小说已不再是一个狭窄的文学类型,科幻思维已普遍渗透到当代多种艺术形式之中,它早已超越了“科幻”的标签和文类的边疆。“在作为一种文类或提供给人观察未来的方法之外,科幻小说已经成为一种理解当下的方式,它正提供着直面和探寻世界、直面和探寻人类对世界之影响的重要工具。”
去年和今年我参加了日本、美国、法国、加拿大的四个科幻相关会议,在会上,各个国家的学术工作者和文学创作者都共同强调,科幻正在越出文学领地走向影视、电玩、主题公园、城市规划、产品设计、战略发展等多种领域,但在此同时,全球性的人才和创意缺乏,正在限制这个行业的发展。
如果中国想要在这个领域迅猛发展且弥补国际空缺,就需要强化自己的创意队伍和创意能力,仅有一部《三体》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大量的科幻创意培训和作品孕育,无论国家层面还是民间层面,都尚未做好准备。此外,在文化环境中放宽对科幻的限制,也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电影审查中对科幻题材的创意应该更放松,而社会生活特别是学校教育中,对想象力的充分自由也应该给予肯定。
今年11月2日,由董仁威等创办的世界华语科幻小说星云奖的颁奖典礼将在北京举行。著名作家韩松担当评委会主席。有关2014年科幻秋天故事还没有彻底结束。对于刘慈欣和《科幻世界》,如何继续下种是季节性的命题,而对于年轻的电影人、作家和科幻学子、教师,未来的一切都还在开创之中。
如何成功地度过暂时寒冷的冬季、如何等待一个新的春季的到来?他们还能找到多少投资让自己的项目延续?他们还能找到多少资料让自己的研究深化?他们还能找到多少人的理解和支持?
——《智族GQ》2014年11月刊
最热文章

对于100年前甚至只是50年前的人来说,今天的城市看起来已经完完全全是一副未来都市的样子

德国概念设计师Paul Siedler的场景创作,宏大气派。\n

所有这些时刻,终将流逝在时光中,一如眼泪,消失在雨中。——《银翼杀手》\n

最近,美国最大的经济研究机构——全国经济研究所(NBER,全美超过一半的诺奖经济学得主都曾是该机构的成员)发布了一份报告,全面分析了 1990 到 2007 年的劳动力市场情况。\n

J·J·艾布拉姆斯显然有很多科洛弗电影在他那神秘的盒子里。\n

我们都知道,到处都在重启;我们也知道,如果有钱,啥都能重启。所以,会不会被重启算不上是个问题,只能问什么时候会被重启。自然而然地,世界各地的各种重启现象衍生出了一个有趣的猜猜游戏:哪一部老作品会是下一个接受这种待遇的?\n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