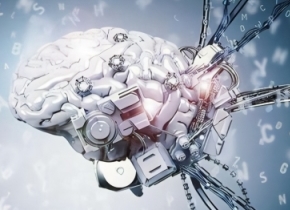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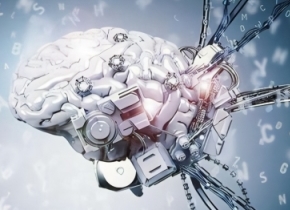


文/任 辉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是哲学史上的永恒之问。但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不知道从何来,不知道往哪儿去,却也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困扰。自农业文明以来,我们的生活范围不断扩大,如何确定自己的方位,成了每个人必须面对的难题。
自然万物的变化总是能给人们带来启发:太阳总是从一侧升起,另一侧落下,东西方向的定义也就由此而来。而夜间的星辰变换虽然复杂,但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北半球的所有星辰都在围绕一个点——北极星做圆周运动,由此,南北方向的定义也由此而生。
但定向和定位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我们要去往陌生目的地的时候,仅仅知晓方向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还需要知道目的地与我们的相对位置和距离。在今天,我们用经纬度坐标可以方便地获取这些信息,但是在远古时期,人们只能通过地标作为参考——小明居住的村落,在我的村落旁边河流的下游;村头大槐树南边50步,就是他的茅屋。这个办法我们至今也在沿用,比如我们问路的时候,对方总会告诉你,往南走,过第二个红绿灯右拐300米就是你的目的地。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地文定位法。
地文定位虽不精确,但在陆地上还是大概堪用的,可随着人类的活动范围从陆地扩展到江海,在缥缈浩瀚的深海大洋上就很难找到可靠的参照物了,所以最早期的航海活动,都只能沿着岸边航行,通过观察岸上标志性的地形、植被来判断自己的大概位置。
生活在南太平洋上的南岛人似乎突破了这个局限,在他们对南太平洋岛屿长达4000年的征服史中,不可避免地会远离海岸航行,那么在茫茫大洋之上他们如何找到陆地和岛屿呢?我们推测,他们通过经验掌握了洋流和风向的变化规律,并学会了以星辰的角度修正自己的航向,甚至可以通过海鸟导向——大多数海鸟会定期返回岸边巢穴,跟着鸟走,就可以找到岛屿。可以看到,以风向水势、甚至海洋生物引路的方式,在波利尼西亚航海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就是所谓的水文定位法。
当然,水文定位对所经过海域的水文环境要求很高,需要有明确的水色变化,或者独特的水生生物作为标记,而这些特点在绝大多数远洋水域都很难找到。更要命的是,水文定位的精确性非常差,指示个大概方向尚可,远距离精确导航就完全不靠谱了。
不过很快的,另一种导航方式逐渐成熟起来,这就是更路导航法。
我们知道,古人通过观察日月星辰,已经可以大致的定位东西南北方向,尤其是指南针发明之后,在海上判别方向已经不是难事。一些早期的航海探险者就把自己远洋游荡的经历汇集成册,编成了《更路薄》。比如一个老水手偶然从三亚闯荡到了西沙并侥幸得以归航,他就会在《更路薄》上记载自己这趟航程中所遇到的一些地标和路程,比如在海南发现的《立东海更路》就有这样一条记载:自大潭过东海,用乾巽驶到十二更。
“更”是古代水手使用的距离单位,1更约等于60里,聪明的水手们会把木片从船头扔下,计算它漂到船尾的时间,用船的长度相除,就能算出船只现在的航速,然后以焚香、沙漏等方式,大致算出跑一更的时间。根据这条更路薄的记载,从大潭(今潭门港)出发,往东南方向(乾巽)行驶了12更(720里),就可以到达东海(今西沙群岛)。
其实大家也能看出,这个方式精确度不会太高,由于风向、洋流的影响,测量出的船速误差很大,而老水手们凭借经验总结出的航线距离和方位,也只是一个大概。东晋时期的法显和尚在天竺学经回国,走的就是海路,尽管水手们使用了最新的更路薄,但法显乘坐的船只还是错过了原本的目的地广州,一直漂流到青岛才得以靠岸。
和纬度不同,经度完全是一个人为概念,在同一纬度上的任何一点,没有任何天文和地理意义上的差别,你完全可以把北京的位置定位东经100度,也可以定为西经100度,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这也让我们无法通过自然特征去测量自身的经度。然而总有一个变通之法:地球24小时自转一周,将这一周等分为360度,那么每个小时就相当于15度,只要知道两地的时间差异,就可以知道两者之间的经度差了。举例来说,如果知道某地的正午12点正好是伦敦的上午10点,那么就说明此地在伦敦东边30度的地方。
根据这个设想,荷兰数学家弗里西斯提出用一个“特别精确的钟”来推算经度。这个钟总是显示陆地上一个地区——比如伦敦——的当地时间,带着它航行,然后测量星体高度角计算出本地时间,再用这个时间和伦敦时间比对,就能知道这个地方位于伦敦东西方的确切经度。这就是“钟表法”。
另一个解决思路方案来自天文学,德国天文学家约沃纳提出利用月亮的移动来测量经度。他发现,月亮在天空中的相对位置每时每刻都在改变,大约每小时移动一个月亮直径的距离。假设从地球各处观察月球在星空中运行的轨迹基本都是一样的,比如月球会在伦敦时间今晚1点刚好掩盖了某恒星A,那么海上的水手在观察到这个现象的时候,就能知道此刻伦敦的时间,只要再算出这艘船所在位置的当地时间(还是观察星体的角度),就能知道自己的经度。这就是“月距法”。
这两个原理看似逻辑清晰,却都被困在了第一步——因为当时根本没有这么精确的钟表,也没有办法预测月球每一天的运行轨迹。以当时的制表工艺,一块表每天快慢个几分钟都是稀松平常的,一趟远洋航行动辄数月,行驶到大洋深处时,这块表所显示的伦敦时间可能就比真正的伦敦时间差了好几小时,而以赤道为例,差四分钟,就是差了1个经度,距离上就差了108公里,如果这块表误差了半个小时,后果不堪设想。而“月距法”面临的问题是,我们当时并没有一张准确的星图,也没有一个公式能准确地推算出月球的运行规律。
在那个科学大爆发的时代,无数天才投身解决这个难题。在英国格林尼治村,天文学家弗拉姆斯蒂德立志为“月距法”描绘一幅精确的星图。他假定天空中有一条虚拟的零经度线,通过夜以继日的研究,一颗一颗地记录下每颗星星通过这条线的时间和所处的高度,就可以画出这张星图。作为一名坚韧的斗士,弗拉姆斯蒂德昼伏夜出,天文台就是他的家,望远镜就是他的眼睛,甚至结婚这件事都差点儿耽误了。
苦心研究了37年之后,弗拉姆斯蒂德获取的数据已经非常丰富,这让迫切需要这些资料来研究月球运行规律的牛顿异常兴奋,但弗拉姆斯蒂德坚持认为这些数据还不完美。心急的牛顿只得指使好友哈雷把资料偷了出来,此举彻底惹怒了弗拉姆斯蒂德,他不仅索回了大部分数据,还负气烧毁了很多设备。1727年,牛顿带着未能破解月球运动理论的遗憾与世长辞。
巧合的是,就在牛顿辞世的这一年,两个年轻人也投身经度难题的破解,分别从“钟表法”和“月距法”两个方面做出了重大突破。
约翰·哈里森本是一名籍籍无名的英国木匠,言语木讷的他却拥有极强的机械天赋和动手能力。他发现,当时最精确的钟,就是在伽利略单摆理论的基础上由惠更斯发明出来的摆钟。哈里森意识到,钟表走时不准确,一部分原因出现在惠更斯的设计缺陷上:钟表的擒纵器在传递发条能量时,总是会造成新的摩擦力,这种摩擦难以消除,又不易量化;在重力恒定的前提下,钟摆的运动频率因长度而不同,那么,热胀冷缩所引发的钟摆长度的变化,也会造成钟表不够准确;最后,传统摆钟也无法规避船只晃动对钟摆的影响。
为了减少擒纵器摩擦带来的误差,哈里森发明了新式擒纵器——“蚂蚱”,这种擒纵器尽量减少部件之间的接触,通过巧妙的力学平衡来达到有节奏传输发条能量的目的;随后,他又发现可以利用不同金属的热胀冷缩比的差别,来抵消气温对钟摆长度的影响;而要解决船身晃动的问题,他设计了一个哑铃状的钟摆,左右两侧的钟摆两端分别以弹簧相连,那么无论那边的受到晃动影响,都会被另一方的抵消,这就最大程度上解决了船身摇晃的问题。
天文学家哈雷和钟表专家乔治·格雷厄姆注意到了哈里森的研究,在他们的资助下,1736年,第一台航海钟——H1横空出世,经过海上测试,H1已经可以把经度确定到2/3度的水平。此后的几十年里,哈里森不断完善自己的设计,相继推出了可以抵消船只转向离心力影响的H2,以及采用夹圈轴承减少摩擦的H3。到了1759年,哈里森拿出了仅有13公分、1.5公斤的H4,引发了学术界的巨大轰动。
同样在牛顿去世那一年,一个20岁的瑞士小伙子继承了牛顿的研究,他通过分析弗拉姆斯蒂德的星图,以数学公式的形式推算出了月球运行的轨迹。这个小伙子就是数学巨匠欧拉—— 一个在眼睛瞎了之后,还可以用心算研究微积分的男人。
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时候,钟表法和月距法的竞争已经白热化,两者都已经做到了理论的初步实现,现在要做的,就是比试谁的精度更高。
1761年,库克船长等多名航海家开始了对这两种定位方法的海上测试,实验结果表明,钟表法和月距法都非常成功。
但月距法还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它需要运行大量的数学计算,一个熟练的导航员也需要算四五个小时才能得出结果,这个复杂的计算过程中出任何差错,都会导致结果谬之千里。月距法的领头人物马斯卡林显然意识到了月距法在计算上的困难,决定采用一种暴力破局的方式——他雇用了一大群学生,提前算好每年的月球轨迹,然后印刷成册子,这样水手们只需要购买当年的数据直接查阅就可以了。1766年,马斯卡林出版了第一卷《航海年鉴和天文星历》,且此后每年都会出版第二年的《年鉴》,这本年鉴甚至出版到了今天。由于《年鉴》始终把格林尼治天文台的位置作为本初子午线,世界各国也不得不接受了这种经度和时区的划分方法。
而哈里森的航海钟也没有停止优化的脚步,1770年,已经垂垂老矣的哈里森推出了再次升级的H5航海钟,英国国王乔治三世马上命令御用天文台对H5进行测试,测试结果非常精确。1776年3月24日,哈里森去世,作为一个一辈子追求准时的木匠,哈里森去世的日期也相当精确——他是在生日那天去世的。
自此之后,人类终于可以准确地知道自己在哪里,要去何方,我们第一次掌握了全球范围内的定位技术。这套经纬度定位方式是如此精确,以至于一直沿用了200多年,甚至我们现在用的卫星定位,其实也是时钟法的一个升级版本。
以美国的GPS系统为例,卫星1它发出信号,我们手里的设备接收这个信号,卫星发给你的信号是什么内容呢?是它上边所携带的卫星钟在发射信号的时候的时间t1,和它所在的太空中的坐标X,Y,Z,你的接收机自己带一个时间t2,两者相减再与光速相除,就是你和这颗卫星的距离。
但在这颗卫星1看来,和它保持这个距离的其实并不止你所在的这一个点,而是所有和它保持相同距离的一个圆。所以你需要卫星2的信号,这样可以确定你在卫星1和卫星2重合的一个面上,再引入卫星3的信号,才可以大致确定你的位置。问题在于,时间总是有误差的,GPS的时间,是通过地面基站上的原子钟,每天更新一次,而你手持设备上的时间,则误差更大,那么就需要引入卫星4的信号,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公式来抵消这个误差。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GPS仪器接收到的卫星信号越多,定位就越精确的原因。
不过,人类的定位需求真的被彻底满足了吗?其实并没有,虽然在地球上,只要有GPS覆盖的地方,我们就不需要再为这个问题发愁,但是,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我们已经征服了大海,接下来,势必就是星辰!
我们现在的很多卫星和飞船,在低于导航卫星的轨道之下的时候,依然可以和地面上一样采用卫星定位,但一些深空探测器,或者我们未来会制造出的星际飞船,则无法享受这个待遇,它们必须找到新的导航方式,而目前看来,脉冲星定位或许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脉冲星在自转过程中,会按照周期性发射稳定频率的电磁辐射,我们可以把它们简单地设为灯塔,尽管我们并不知道这座灯塔和我们的相对位置信息,但我们可以在地面或太空设立三个观测站,用脉冲星信号到达各观测站的时间差,算出脉冲星与地球的相对方位,而通过对不同方向的多颗脉冲星信号测定,就可以获得脉冲星列阵。那么和航行在海上的船只一样,我们只要有一台足够精确的钟表可以记录地球的时间数据,再把飞船上接受的脉冲星信号与地球数据相对比,就可以算出飞船相对于脉冲星或地球的位置。
我们现在回头来看看,人类一路走来,先是不知东西,继而学会了根据太阳星辰分别方向,随后可以利用地标和方向行走四方,然后战战兢兢地沿着海岸踏入了海洋,又壮着胆子用天文、海文知识慢慢走向深海,再通过星空定位了纬度,最终在激烈的角逐中确定了经度……直到今天,我们掏出手机,就可以很方便地指示任何方位。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为了解决这个关于定位的最初问题,汇聚了全人类顶级的智慧,推动了无数个行业和科学门类的发展,甚至还将在更为久远的未来持续地探索下去。
让我们回到开头的那三个问题: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些问题可能永远没有答案,但波澜壮阔的人类文明史和闪耀的群星又仿佛在回应:“真理的大海,让未发现的一切事物躺卧在我的眼前,任我去探寻!”我们为探求未知而来,前行的步伐,就是我们的命运。
最热文章

潘多拉,让植物动起来!——植物运动的科学与幻想

防患于未然——犯罪预测算法能够实现吗?

种菜不易:一帆风顺的科学幻想与月壤实验的挫折

【榕哥烙科】第537期:进化的速溶咖啡,如何越来越醇?

“瓷韵中秋,科技添彩”——2024年中国科技馆陶瓷主题中秋专场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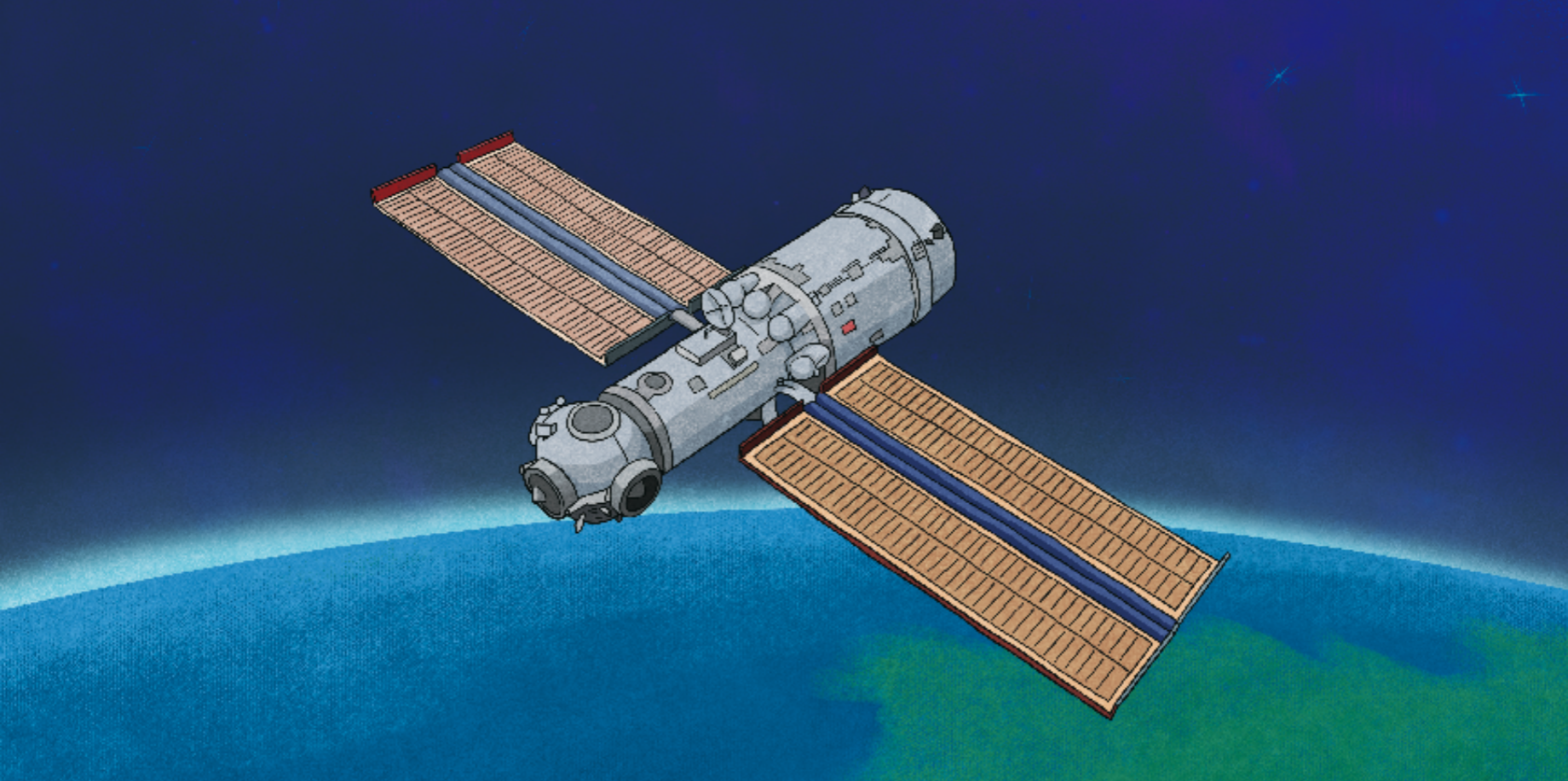
守时大神——空间冷原子钟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977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977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