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彭超 图/禄水
××××年11月27日 大雪弥漫 沃森和克里克
从前天开始,使用陶瓷过滤器,反复了近几十次筛选分离,那些标记过的双螺旋结构才重新回到了我们的视野——它们被编辑得更为复杂,驱动着神经系统以一种不可逆的方式不断扩张。这本该通过子代变异,且只在胚胎期发生一次,如今,一切扑朔迷离——的确,“无量”是一种基因药物,但即使其效力再强大十倍(前提是受体能有如此大的耐药性的话),也不足以突破遗传限界,产生这种驱动力。
太阳房外,暴风雪已经持续了整整三天,愤怒的雪和风不断地拍打着这栋柔性材料编织的屋子,它会因此轻微摇晃,像个温暖而静谧的白色泡泡似的,我们每天就在这个泡泡里工作到很晚,又踩着没膝的白雪回到临时房车营地,中间不足十米,但每一步都仿佛行走于一座风雪迷宫。以及那些罐头食品和脱水蔬菜,折磨着我的关节炎……然后是梦,梦里尽是学会用火的土拨鼠,他们形销骨立,眼中满是痛苦,开始制造工具,陶瓷、家具;接着便是武器、飞船、超级计算机,而随着他们制造的东西越来越先进,他们的枯槁、痛苦也就越深,最后干脆什么也没有了,只剩下臃肿的土拨鼠从冬眠中醒来,看起来没有任何聪明可言。
深夜,被响亮的风雪声吵醒,韩炽也没睡,便聊了起来……
又一天就这么消耗在太阳房里;大雪不断制造出簌簌的声音,但风却变得微弱了。
临近夜晚,我们所掌握的数据已经足够,便开始通过计算机建立进化数据模型,其中一个模型的预测匹配度达到了百分之七十五,我们便首先阅读那份建模数据。
是耶尔森菌,制造鼠疫的真正元凶,一些突破了脑血屏障,以某种我们尚不清楚的方式与“无量”融合。正是这种细菌使得“无量”具有了传染性,而“无量”则使得耶尔森菌不断进化——是一场耶尔森菌和“无量”基因之间的生存博弈,就像噬菌体和病毒,他们通过不断进化来避免自己被对手吞噬。本质上,则是不同基因的生存之争,因为基因的目的总是最有效且最大化的存续。耶尔森菌说到底是一种蛋白质外壳包裹的基因,土拨鼠体内则是另一套。
因而,土拨鼠族群的日渐“聪明”不过是这种生存进化的副作用,与此同时,耶尔森菌也在变得强大,随时可能脱离束缚,所以,越聪明也可能意味着越短命。
“这不可能!”
“这种进化和融合可能涉及脑血屏障的免疫策略。”
“耶尔森菌已经偏离了方向,问题是这可是存在了上亿年的细菌。”韩炽说。
我明白他的意思,在上千年人类接触史中,除了造成无数的恐惧与死亡,为什么它们从未偏离方向?
我回答不了,除非我们对进化中的两种基因重新测序。但我什么也没有说,因为测序工作如此庞大,显然不是我们俩都够完成的——这意味着我们得上传数据,报告发现,于是,一切又都回到了老路子上:我为什么不提交研究报告?
“你不用这么看着我,说说你的想法。”
“你知道我想说什么!”
我想了想,“谁会被派到这种偏僻又寒冷的地方,待上整整四个月?”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可以报告,直升机说不定今晚就能飞过来,但我们会被派到更偏僻更寒冷的地方。”我说,看着这个年轻人,他摇着头,显然不相信我的话。
“你不过是个新手,我也不是谁的亲信,你认为我们发现的是什么?你认为这是一家商业公司还是慈善机构?我现在够头大了,你自己动脑子吧!”我说。这次,他没再摇头。
“的确,光凭我们俩没法测序,这不过是说我们无法合作一篇论文在《科学》上,但如果再有一些实际证据呢?我们可以投给《自然》,到那时候,你我就是沃森和克里克。”
“沃森和克里克!”
“对!沃森和克里克。”
××××年12月5日 渐晴 凌晨,终于找到了那罐茶叶
又做了那些梦,聪明到已经极度危险的土拨鼠,正在将我和韩炽肢解。从床上醒来,我意识到自己忽略了一个问题:这些土拨鼠究竟会聪明到什么程度。
他们制造了捕鹰陷阱,他们克服恐惧学会了用火。古猿人也会制作陷阱,学会了用火,但他们进化了上千万年才稍有了点儿聪明劲。但我却没有在黑暗中说服自己,毕竟进化太快,已经不可能以常识生搬硬套。我想就此聊点儿什么,这年轻人却在安静的黑夜中酣眠。我朝窗外望去,暴风雪停止了,月光倾泻在绸缎般起伏的雪面之上,远处,是那座通信塔,通信塔下方的哈鲁曼洞穴也被雪覆盖着。
我穿好了羽绒服,离开房车,来到太阳房,重启了一部分设备,但没察看那些数据,而是为同步通信设备设置了密码权限,这样,韩炽想要发送任何报告回总部都得先经过我。之后,我拿出了另一台动力昆虫设备,也是最后一台,放飞。它在无风而干燥的凌晨时分,穿过明亮月光下更明亮的雪,爬到了通信铁塔的基座,又从一处凸起的出风口钻了进去。
这时,距离上次钻进这里已经过去了四天时间,比起某种忧惧,反倒更多期待。我很小心地操纵动力昆虫,经过最上面的冬眠洞和临时洞——那里还有一台远红外摄像机,不过已经很少拍到土拨鼠的踪迹,他们如今都在更深的地下活动,动力昆虫沿着倾斜的穴道而下。
我没想到会看到一座明亮的“大厅”,足足有一米多高,超过五十个平方,洞顶呈半弧形,弯曲的墙壁上挖出一个个对称的孔洞,里面是小小的火堆。地面上则平行一条条浅浅的凹槽,宽窄恰好一只土拨鼠通过,而他们则有序的穿梭其间,来往于洞壁上的各个洞口,没有堵塞,似运行良好的程序。但这程序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显得瘦弱也枯槁,我猜,进化让他们变得更聪明,也折磨着他们;他们来来往往,其中一些爬出了槽道,来到了“大厅”尽头处的一面墙壁,墙面上尽是些佛教石窟似的小孔。
我指挥着昆虫朝那边去,尽量避开土拨鼠,爬过角落里一堆凌乱的白色物质,起初看不清楚是什么,但动力昆虫调整了红外参数,才发现,这是一对羊的骸骨,骸骨上布满齿痕。从那里也能看清尽头的石窟墙其实是一张角度有些倾斜的元素周期表,并不怎么规则,但每个格子的上面都用砂石标着元素名称,字母都有些朝左倾斜,且歪歪扭扭,有些元素的格子里放着东西,例如Cu里放着一枚暗黄色的纽扣,C里是一截烧焦的鼠尾。但三分之二的格子里什么都没有,另外三分之一被填满的格子中有许多放的并非是正确的物质。
最后一种元素倒是完全正确,格子上写着money,下面放着一枚一元硬币。我的视线离开屏幕,抬起头来,太阳房内,那张元素周期表正投影在内壁上,最后一种元素也是money,那是韩炽的杰作——我现在还不清楚他们是如何归纳并产生出了这些概念。
我在太阳房内,带着困惑,站起来,往右移动了几步,现在,因为视角和投影角度,墙面上的那张周期表也朝左倾斜了。
我望向身后,是一圈棱形挂柜中的一只——既用来支撑太阳房,又用来储存物品,这样的柜子整个环绕着太阳房的中部,大约有三十来个,而我根本记不清这只柜子里放着什么。我走过去,掀开来,是一罐“雀舌”和一只正盯着我的看的土拨鼠——是哈鲁曼,手里紧握一根鹰的尾羽,就像握着一根权杖似的。
我脑袋有些发麻,现在,即使在我写下这些时,这感觉依然没有褪去。那已不是一只常识中的土拨鼠,脑袋比之前更大,毛细短、稀疏,呈灰色,肩膀也更宽,在肱二头肌到外肩之间隆起浑圆的肉瘤,看起来十分怪异。他的整个身形也更为精瘦,爪子退化了,前足的四趾进化得更长,包括原本毫无用途的拇指,后足也经过了类似的进化,本该装在后足上的追踪器也不见了踪迹。
他缓慢而轻柔地从柜子里爬出来,身形轻盈,但每走一步脸部都痛苦地扭曲起来,我猜,这或许正是基因博弈所带来的痛苦——但这时我最在意的并不是这些,而是他像窃贼一样地溜进了我的地盘,不知待了多久,偷窃了多少知识与概念。此刻,他却对我全然无视,好像早就料定了我不能把他怎么样。
他就这么离开了,我想阻拦但始终没有动弹,看着他爬上门框,打开门之前,我叫他的名字——哈鲁曼。他没有回应,我又叫了一遍,寒气已从门缝里灌了进来,门外则是绸缎般、明亮的雪,哈鲁曼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消失在雪地里,连个脚印也没留下,但太阳房内的监控却拍下了所有。
我有种不切实际的挫败感,正是这挫败感让我稍稍理解了布鲁克特,也自然想到了这个孤独的牧人,心想着,他的怒火或许已经差不多褪去了。
而天空和大地是那么的平静,等到我一觉醒来,太阳房外又是无尽的阳光;韩炽正坐在另一台电脑前浏览着数据。“看你睡得熟就没叫醒你。”他说。
“睡不着,过来整合了一下数据。”
“有什么发现吗?”
我摇摇头,站起来,打开柜门时深呼吸了一次,那罐“雀舌”还在,我打开嗅了嗅,确定没什么异味,才为自己倒上了一杯,坐在电脑前,和韩炽一起整合数据,并将其中的一些翻译成英文。数据总是那么的枯燥冷漠,根本无法反映出某些时刻的直观感受——那些骄傲的、该死的土拨鼠,我忽然对于正在做的事情没有了一丝优越感,即使这是一篇有资格出现在《自然》上的学术文章。但我的感觉,或许和布鲁克特被三只着火的土拨鼠扑倒时没什么两样。
下午时,我本该和韩炽一块去拜访布鲁克特,但他坚持做完手头的工作,我没有强求,毕竟,他有他的专注、理由、优越感。而我则带着某种感受敲响了那扇厚厚的木门。
那时,我还不知道这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错误不在于拜访这个牧人,而是带着这种感受去拜访,并试图与他分享,误以为这可以化解什么,而烈酒又加深了这种自信。
他打开门,极不情愿地将我放了进去,屋子里暖烘烘的,屋角依旧摆着那副鹰架,但上面已经空空荡荡,整个屋子也显得昏暗而空荡,我看看眼前那个牧人,看上去和上次见面时没什么变化——没有傲慢,也没有热情——但谁又知道他的内心是怎样的呢?直到一番尴尬的寒暄之后,他拿出了那些烈酒急于找人分享。
我说,布鲁克特,这世上会有更好的鹰。可他什么也没说。
我说,布鲁克特,等到大雪解封这一切就会过去了。他什么也没说。
我说,布鲁克特,至少想一想春天温暖的日子吧!想想女人!他什么也没说。
我说,布鲁克特,你什么都不说,只喝酒,是因为还在生气吗?
“不!”他说,脸上红通通的,又给自己倒了一杯,“我在想我的鹰。”
“很抱歉发生了这种事情。”
“为什么要抱歉?”
我告诉他,我知道在南疆有些很好的驯鹰人。
“不会再有那样的鹰了!飞得高,却中了这种陷阱,拖进了地洞里,一只鹰——”他停了下来,让呼吸缓和下来,“一只鹰被拖进了地洞里,它会害怕吗?”
我心头一惊,意识到自己面对哈鲁曼的感受是什么了,如此简单,可作为一个人却很难承认。
像布鲁克特这样的牧民则更难,我猜,在他被三只土拨鼠扑倒的夜晚,他害怕了。此时,他还在说着关于鹰的那些话,怀念一点儿什么,但所有这些怀念的本质都是在拒绝另一些记忆。他也谈到了勇敢,勇敢对于这样的人而言,几近自身道德的一部分,而他的怯懦,就像是我们的道德缺失。
幸运的是,那些“害虫”再也不会钻出地面了。他告诉我。
可那时我也喝了很多酒,想要倾诉那种感受。起初,我为哈鲁曼家族辩护,接着,我便讲到了我的害怕,不是那种对于某个人或者某件事的害怕,是对一些抽象的东西:看不清的病毒?凌驾于我们之上的“野蛮”?我说不清楚,但我告诉他,那种感觉从我看见哈鲁曼洞穴中那堆羊的骸骨时就开始了……看见哈鲁曼握着一只鹰的尾羽时则更甚……
我喝多了,说了很多,无关于那些实验,我的抱负,而我以为布鲁克特这样的人会明白……我们又继续喝,恍恍惚惚的,他问了我很多问题,是关于这些土拨鼠的,但具体我不太记得了,只记得他没有挥刀舞蹈,只记得他的严肃。我沉睡了过去,醒来时,右手麻木而疼痛,等我睁开眼睛,看见了自己的小拇指,却在桌子的另一端,中间则隔着好大一摊干涸的血。
××××年12月6日 晴 入侵
牧羊人死了,就在那个我们都喝醉的夜晚,他剁断了我的小拇指,又开着车来到了塔基下方,这一次,他不仅仅用到了更多的汽油,还包括毒药、乳化炸药。他先将炸药从几个洞口灌进去,爆炸在铁塔旁掀起了一个大坑,破坏了塔基,使得通信塔朝着另一侧倾斜,而那个通信塔下的摄像头也被破坏了。
后来,他大概还将汽油灌了下去,土拨鼠所设计出的洞穴回路则使得这些汽油回流,在他点燃的一刻,他所站的位置,反倒瞬时成为一片火海——但真正让他死亡的却不是火,而是猎枪,一颗子弹从他胸口钻了进去,在背后开出一个大洞。
韩炽来到现场的时候,布鲁克特已经是一片焦黑,枪离他足足有五米。
韩炽叫醒了我,当看到焦炭似的布鲁克特时,我对断了一只小拇指的愤怒也就没那么强烈了。我们没有爬下坑,寒风或其他什么东西让我们瑟瑟发抖,只得回到太阳房,启动同步通信,第一次却输错了仅有四位的通信密码,第二次也错了,我不得不停下来整理混乱的脑子,第三次终于输入正确,却发觉根本没有信号。而幸好还有一部卫星电话,放在手术云台下的那个密码箱里,但那里什么都没有了,包括备用的其他仪器。
我们找遍了整个太阳房,也没找到。
“可能在房车营地。”
“算了,不可能找到了。“我说,直到这时才开始处理伤口,发觉自己抖得厉害。
“我们该看看通信塔。”他建议说。
“能修好吗?“
“主体没有受损的话,问题不大。”
于是,我们又来到了那座被炸歪的通信铁塔下,拿着两罐瓦斯喷雾。铁塔下的陷坑空空荡荡的,布鲁克特焦黑的尸体和那杆猎枪都不见了。我俩愣了好一会儿,但谁都没勇气爬下去看个究竟,最后决定先修复通信铁塔再说,韩炽爬了上去,我抬起头来就这么看着他,天空蔚蓝,阳光明媚,可周围的一切都一派死寂。他站在铁塔上鼓捣了好一会儿,爬下基座,摇摇头,又开始修复基座上被炸成两截的远红外摄像头,连接线路,缠上几圈绝缘胶布,最后摄像头的红色指示灯又开始闪了起来,他回头比出一个“OK”,结果,脚下一滑,整个人都滚进了那个陷坑里,一只手摁在泥土半掩的洞穴口,他几乎条件反射般地远离了洞口,开始慌乱地朝上攀爬。
我想对他说点儿什么,可感觉喉头发干到一个字也吐不出来,不得不咽了口唾沫,看着他艰难地爬出来,却始终没搭手拉他一把。
等他爬出来后,我们远离了陷坑,他忽然说:“这一切本可以避免!”
我知道他想表达什么,没有回应。结果,带着骂腔,他又说了一遍,对着我。
“现在不是谈论这些的时候。”我说,一点儿也不想和他争论。
但他的眼神不依不饶,有愤怒,也有害怕。不知为何我就是能感到他的那种情绪压迫着我,等到接近太阳房,我开了口,“开发这些药的是卓越公司,派我们来的也是卓越公司。”
“可不报告的是你,让基因失控的也是你!”
“你反对了吗?”我说。
我们进了太阳房,他继续寻找那台不可能再找到的卫星电话,而我则找到止痛药,拆掉止血带,发现伤口比我想象的严重。我望了望韩炽,和先前一样,他不在意,连问候也没有。于是,我重新包扎,处理完,将一副皮手套戴在手上。
也就是那个时候,通过铁塔下刚修好的摄像头,我们看到了那场仪式。
一只土拨鼠钻了出来,接着是另一只,陆陆续续十几只爬出了洞口,站在另一边,他们看起来和我那晚见到的哈鲁曼区别不大,四趾长到与手臂不成比例,上肩处隆起着,而大腿外侧也都结出了神经瘤,每行走一步都面容扭曲。
他们在冬日温暖的阳光下围成半圆,其中一只穿过了整个群体,站在了陷坑的最中央,背部正对着屏幕,因此可以看到V字形的标记,但现在,通过这种方式区别哈鲁曼毫无必要,因为,不仅仅是他,周围几乎每一只土拨鼠的背上都多出了一个这样的标记。
铁塔上的“哨兵”发出了浑厚的叫声,第一波土拨鼠开始围过来,十几只,以中间那只为圆心,背对着,围成一圈,翘起尾巴,在毛色泛黑的末端,分叉出蓝色的神经线,舞动着,就像是从尾巴里钻出来无数条蓝色线虫,渐渐将中心的土拨鼠整个包裹起来。
接着是第二波,在第一波外围围成一个圈,竖起自己的尾巴,让内部的神经线发散,蔓延到他所背对着的同类,覆盖到他的面部、大脑、肩部和腿部的神经瘤中……这样足足围了四圈,整个族群开始剧烈地颤抖,带着某种无法理解的扭曲,有种同一性,仿佛他们已经成为一体,阵阵歇斯底里,如同黑暗的心脏,某种邪恶的宗教。
韩炽将视频数据转存了出来。我给自己倒了一杯茶,发觉拿杯的手不住地抖,只好换到另一只。那时,我们谁也没谈论画面中的内容,而是选择谈论离开这片冬季草场的可能性:包括五百多千米被大雪封堵的公路(这还只是乐观的估计),至少五处海拔五千米的达坂。结果,我们还是认为修复通信设备更现实一些,韩炽再次检查了一遍,软件没有问题,硬件也完好无损,于是,我们那天所面对的问题便是:当你发现一个系统毫无瑕疵时,你又如何去修复。
然而时间在这几天被浓缩、混合,从上个月二十八号到这个月三号,五天的时间,感觉好像经历了很多,又似乎只有寥寥几件事,而布鲁克特的死后发生的一切又总难分清先后次序。或许那场哈鲁曼家族的仪式发生在另一天,我们看见那些羊在前,至于布鲁克特尸体不见也可能在这之间或者之后。
总而言之,在那几天发生的事情中,我们看见那些羊是其中一件:
一共有五只羊,出了畜牧栏,沿着草线缓慢地走着,没有一只停下来吃草,当距离我们足够近时,我们看见了骑在羊背上的土拨鼠。它直立着身体,眺望着天山,好像一切都理所当然——那种姿态让我想到了布鲁克特。五只羊是如此顺从,直到接近铁塔后,土拨鼠们指挥它们钻进已经被拓展过的那处洞口时,打头的羊才将前蹄抵在洞口始终不肯钻进去。五只土拨鼠则从羊背上跳了下来,朝着洞内呼唤,没多久,传来一阵不那么响亮的吆喝声,那些羊便克服恐惧,钻了进去。
吆喝声来自布鲁克特,即使站得远我们无法确认,但过后通过远红外摄像头收集的声音,我们能百分之百的确定。
在那之后,一只哈鲁曼(现在,我们已经不再称他们为土拨鼠)敲响了太阳房的门,在我们打开门后又大摇大摆地离开,在门口,放着一枚硬币、贝壳化石和一小筒乳化炸药。
××××年12月7日 晴 图腾
第二天,迎着晨光,我们看见了一个圆形的土墩出现在铁塔下方,高度已经接近了塔基,几只哈鲁曼便在这上面忙碌着,将更多泥土夯实到土墩上。他们的神经瘤不再那么明显、臃肿,因而异常灵活,他们用尾部作为支撑,而注意力似乎可以兼顾三到四种不同的工作:右脚和着泥浆,左脚传送工具,另一前肢则将泥浆倒上去;就好像他们天生就是熟练的筑墙工人似的,不仅如此——还是三到四个建筑工人合为一体。
这工作一直持续到正午,现在,我们已经能大致看出这建筑的轮廓—— 一座有着浑圆底座的金字塔,底面积比这座通信铁塔的底座要大上一倍,塔上面满是蜂巢似的孔洞,大小足够一只哈鲁曼通过,最下面,则是一道半隐于地下的洞口,足足有一米,像张半张开的圆嘴似的。整个建筑感觉有点儿奇怪,即使以泥土为材料,但绝不丑陋、粗糙,而是光滑、对称。
我们就待在远处,不敢靠近,看着一层层地搭建起来,算不上恢宏,却足够精致、繁复,塔身表面过多的孔洞,蜂巢似的,但恰好的比例却使其另有一种秩序,在冬日阳光中,如草原上忽然耸起的另一种图腾似的。
××××年12月8日 晴 不谈论恐惧
我听到那种声音从清晨的迷雾中传来,是一种轻而柔的叫嚣声,有着旋律般的起伏,但这旋律古怪,让我感到一种漫长的分裂与融合,在脑子里、身体中不断地持续着。
“你听到了吗?”
韩炽从房车内另一张床上爬起来,点点头,但似乎并没有我那种形而上的困扰。“一些风声而已!”他漫不经心地回应。
等到大雾散去,那声音还在不断响起,音源来自那座刚刚建好的圆底金字塔,当微风穿过孔洞时,那些声音便间或响起,仿若发自于很遥远的时空。一处古老的洞穴中,某种质地坚硬的襁褓。
这让我一度着了迷,等到我从这种声音中彻底醒过来,阳光已经明媚到晃眼,我们用过早餐,拖延了好一会儿才前往太阳房内,仿佛那些研究已经不重要了似的。等我们输入密码打开太阳房的门,便发现研究的确不重要了,因为整个太阳房的仪器几乎都被搬空,只剩一圈棱形吊柜和零星的仪器零件。
“谁干的?”
方圆五百千米只有我们和那些哈鲁曼,我倒是想知道他们是如何干的,最重的机器得有好几百千克。我抬头环视着监控,连监控也被他们拿走了,也包括电脑,研究DNA的所有仪器。
韩炽纠结了好一会儿,“那些数据!”
“我备份过了。”我说。
“在哪儿?”他环顾四周,没看到一台电子设备。
“在房车,那台私人笔记本里。”我说,“你不用这么看着我,我只是想休息时能研究一下。”
然而,不仅备了份,还建立了一套局域网络,和实验室里差不多所有的设备,因此我可以实时同步,我们回了房车,打开电脑,可那边的电脑和仪器都没有启动,我们茫然地看着电脑。
“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我不知道。”我说,“但可以肯定,这是一种很痛苦的进化,没有一种生物会喜欢痛苦。”
“我也不喜欢。”
我看着韩炽,他脸色苍白,眼中满是血丝,看起来很迟钝,“放轻松。”
“这还只是十二月!”他说,现在,他忍不住和我探讨这些了。
我告诉他或许哈鲁曼进化不到那个时刻,或许耶尔森菌会占了上风。
“然后呢?”
“放轻松,你现在最该做的就是睡上一会儿。”我说,看着这个年轻人,看起来永远都不会拥有睡眠了似的,但他最终会睡着,无论将来面对的是什么,那些害怕的事情如何折磨着他,一个人都不可能永远醒着。
××××年12月14日 阴 洞穴
今天,他们终于重启那些设备了,我点击了同步,那一头的摄像头悄然开启,一只哈鲁曼出现在屏幕里,由一根半弯曲的金属棍吊在离地大约十几厘米的空中,横在笔记本前,脑袋歪向屏幕,四肢一共十八根指头在键盘上飞快地移动着。
他身后,整个空间比我上次所见时大了至少一倍,整洁,简约,一种顶端分岔的金属片发着光,在高约一米半的洞顶排开,每一片都很微弱,但加在一起便足够明亮。显然,他们已经接通了那条输电线路,那是冬季到来前,公司联系自治区的电力局所架设的专用线路。那些线路的另一端便接在实验仪器上,仪器凌乱摆放着,几只哈鲁曼则爬行期间,似乎正研究着。
仪器上方是那张元素周期表,已经高级了许多,每种元素的名称都由浅红色的涂料所标注,没有了money这种元素,三分之二的格子里都放上了物品,多半都与标注的元素对应。
洞穴的地表则是一片道路网络,由条条浅凹槽所组成,繁复如集成电路,许许多多的哈鲁曼就穿梭其间,从特定的出口出来,或从特定的入口钻进凹槽。这些一直延伸到洞穴的远端,一处微微隆起光滑、规则的圆,圆心要高出整个地表一些,在最中间的那个点,插着一根鹰的尾羽,祭坛似的。
距离“祭坛”不远,是一座有着半圆形门洞的仓库,里面,堆积着贝壳化石,不多的硬币,以及整齐码放的乳化炸药。门口是两只哈鲁曼,不时有他们的同类从地面浅浅的凹槽钻出,递上一枚贝壳化石,或领走火腿肠似的乳化炸药。
之后,我们联通了操作界面,这台电脑正疯狂地运作着,一层层的窗口闪烁着打开又关闭。
“他们在互联网上。”韩炽说,带着点儿绝望。
“网络已经断了!”
“对!我们的已经断了。”他说,调出了二十四小时以内的cookie文件。
浏览和下载的痕迹杂乱,包括政治评论、论文、电影和2014年NBA总决赛以及成人网站……你很难从他们的浏览中抓住一个重点,仿若他们就是互联网世界的饕餮,迅捷而贪婪,一切就这么持续到深夜,说不清楚我们现在的行为是研究还是窥探。

刊登于《科幻世界》2020年11期
最热文章

完美人生

隐形时代(下)(1)

隐形时代(上)(1)

【榕哥烙科】第537期:进化的速溶咖啡,如何越来越醇?

“瓷韵中秋,科技添彩”——2024年中国科技馆陶瓷主题中秋专场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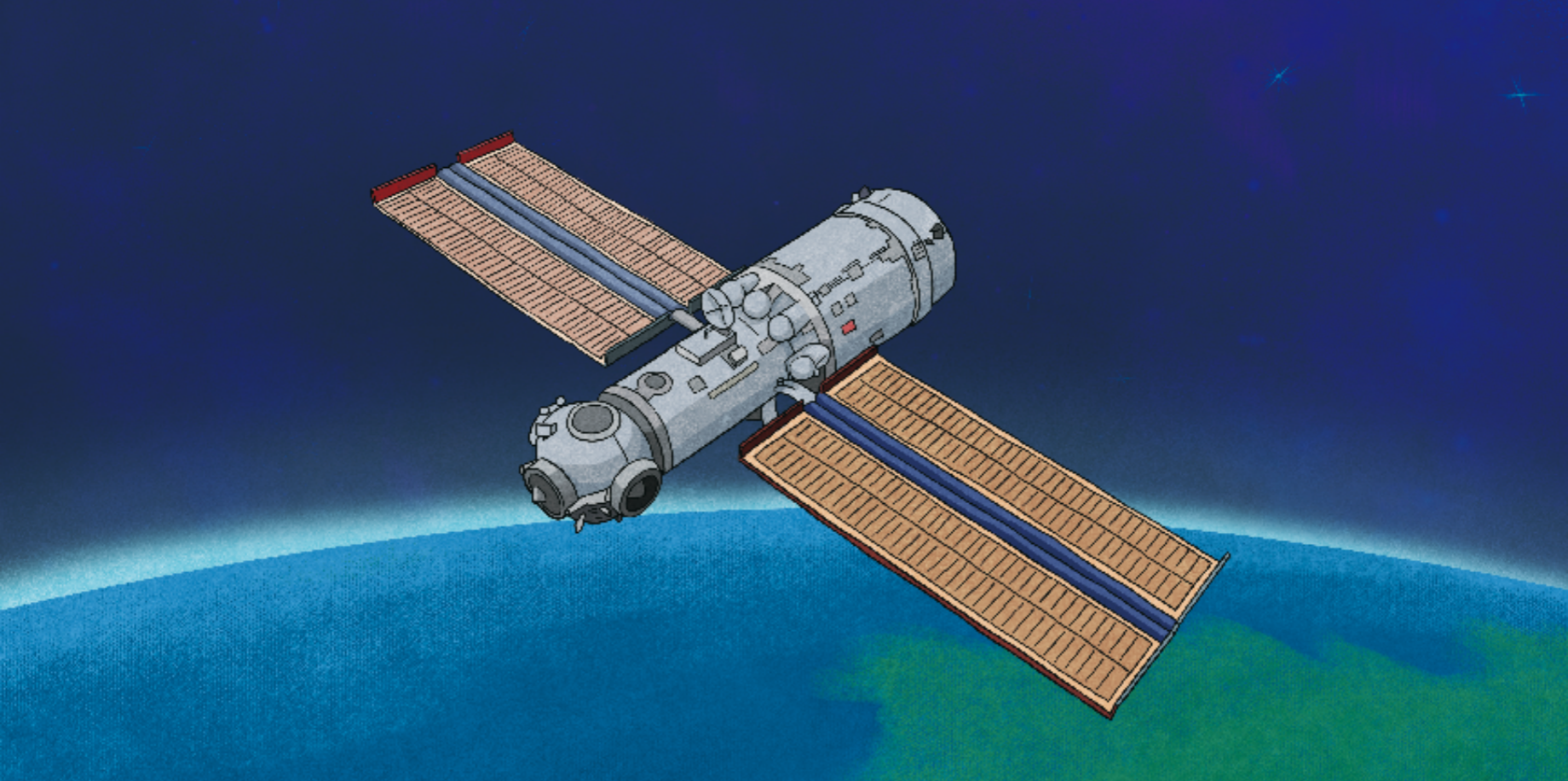
守时大神——空间冷原子钟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977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977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