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彭超 图/禄水
××××年11月23日 晴 他们渐次醒来
哈鲁曼醒了过来,在黑暗的冬眠洞内活动着因蜷缩过久而僵硬的身体,他还没能完全适应,轻嗅着,在他身下,几股淡淡的暖意如一座岛屿似的围在一起,呼吸一张一翕,来自他的三个妻子和四个孩子。此刻,他们尚沉于漫长冬眠,而他无端地醒来,在这黑暗中渐渐地适应,沿着洞穴边缘,爬过几个孩子的身体,一条倾斜的过道,顺着气息,来到了更浅的夏季洞。
在那里,储备着针茅草、隐子草和一些少得可怜的草籽。这些本该是他们四月醒来时的过渡食物,但此刻,饥饿和愈发的寒冷让他已顾不得这么多,开始用笨拙的前肢抓住草籽,机械、迅速地啃食起来。
他停止了进食,半立起身体,爬到洞口,探出脑袋,一切尚处于清晨时刻的微暗之中,大片大片的起伏草地如今已被厚厚的积雪覆盖,起伏的最顶端,狂风卷起了干粉似的雪尘,在零下二十多度的低温中,像一股股凌乱而干燥的火。
即使有着厚厚的绒毛,这世界对于哈鲁曼而言还是过于寒冷,他缩了回去,回到夏季洞,半立身体,那一刻,就像个人似的思考着;他的一个妻子在不久之后醒来,背部有一撮不那么明显的白毛,那是茉莉;她也适应了一段时间,便在夏季洞和哈鲁曼汇合了。
接着是另外两位妻子,她们的醒来扰动了冬眠洞中的温暖平衡,那四只当年幼崽也就自然而然地醒来了——此时冰雪几乎覆盖了目之所及的一切,植被萎缩,气温最低已接近零下四十摄氏度,而他们所剩下的食物只够维持三天。哈鲁曼和他的族群回到冬眠洞,彼此靠得更拢,用尖利而迅捷的声音传递着信息,直到接近正午,开始了轮流工作。
工作的唯一方式是朝着更深的地底打洞,当年幼崽负责将多余的泥土运送出去,哈鲁曼和他的妻子们则负责挖掘——那是枯燥的工作,在屏幕前看得我昏昏欲睡,但韩炽提醒我说,很少有土拨鼠会将地洞打到地表五米以下,而现在,根据哈鲁曼和茉莉脚上的追踪器测算,他们已经深入到地表十米以下。
“或许下面更暖和些吧!”我当时对他说,摇了摇空空的茶叶罐,问他还有没有茶叶。
“我不喝茶,有速溶咖啡。”
我把空茶叶罐扔了出去,打在柔软的内保温层又弹了回来。
“要吗?”
“你留着自己喝吧!我搞不惯。”我说,脑子里隐隐觉得哪里应该还有茶叶,像某个神秘的线索似的,就要浮出水面时,韩炽打断了我。
“或许我们该派出一只动力昆虫,看看他们在下面干什么。”他说。
之前,为了观察哈鲁曼家族,我们一共安装了四枚微型远红外摄像头,分别位于三处洞穴和距离洞口不远的通信铁塔下方,但我们没法看到最下面的情况。动力昆虫则可以携带着微型摄像头。
那是很昂贵的设备,而且现在使用还为时尚早。我喝着白开水告诉他,感到这半圆形太阳房开始轻微地摇晃起来,外面有什么不断地碰撞着由柔性硅层组成的外墙。我穿过保温通道,看到了几百只略显慌张的羊,布鲁克特骑在一匹高大的枣红色骏马上,戴着一顶厚厚的熊皮帽子,左手执缰绳,右手横举胸前,那只哈什赫鹰就站在他右小臂上,在正午明亮的阳光下,羽翼就像打过一层蜡似的泛着光。
“呀!布鲁克特。”
布鲁克特骑在高高的马上,看看韩炽和我,什么也没说,没有傲慢,也没有热情。除非喝多了酒,这都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牧民,你不知道他平素里的想法,或者根本没有任何想法。每年十一月到来年的四月大雪解封以前,他都待在这样的冬季牧场,至少有十五年,前一半的岁月由他的妻子陪伴,后一半的岁月,就只剩这只日渐苍老的哈什赫鹰。
此时,这些羊已经沿着丘陵那缓缓的斜坡而上,在背风面厚厚的白雪上踏出了一条道路,布鲁克特已经来到了丘陵平坦而宽阔的顶部,手举猎鹰,远眺着白色火焰般凝固的天山,脚下,经过一整个夜晚的狂风,丘陵顶部的积雪被吹散,露出短短的金黄野草,羊群们正是朝着裸露的草地而去。我和韩炽也紧随羊群之后,爬上了顶。
天空一片蔚蓝,不远处,布鲁克特正驱赶着羊群。我能看到远处的天山,连绵不断的冬季草场,以及那座通信塔——哈鲁曼家族的洞穴就在通信塔的下方。
“快看!”韩炽把另一架望远镜递给我了。
是哈鲁曼,已经离开了自己的洞穴,正穿过一片厚厚的积雪,爬上另一座起伏丘陵的顶端。在蓝宝石般美丽的亮空之下,他看起来不似洞中的哈鲁曼,但背部那撮V字型的白毛和圈在右后肢的追踪器使得我可以肯定这就是哈鲁曼。
围绕着下腹部及背部的一圈浑圆脂肪不见了,不再臃肿的他敏捷地奔跑着,看起来像某种具有危险性的动物似的。
“他脱毛了。”一旁,韩炽提醒我说。
“不可能!”我说,用望远镜看得更仔细:他的确脱毛了,毛灰而稀疏,而没有一只土拨鼠会在冬季脱毛,当然,也没有一只冬眠的动物会在冬眠不到两周之后就醒来。
“这简直就是自杀,他没法扛过这个冬天的。”
“哈鲁曼不是普通的土拨鼠。”
“他现在在干什么?”
我没有回应,继续观察着,看他沿着丘陵的草线奔跑着,越过了自己的领地范围,在另一面向阳的坡地上用尾巴撑起自己的身体左右四望;不远处,另一只土拨鼠站在坡顶看着他——此时,我才意识到,在这个冬季醒来的可不止哈鲁曼一个族群。
坡顶的土拨鼠朝着哈鲁曼叫了起来,类似浑厚的鸟叫声,应该是某种警告,提醒哈鲁曼越过了自己的领地,但他不为所动,朝着坡顶奔跑起来。那叫声因而更为急促,召唤出了另外两只土拨鼠,其中一只肥而壮硕,首先朝着哈鲁曼的方向爬去,另外两个旁观者则接连不断的发出连续和激动的叫声。
现在,哈鲁曼和这片领地的男主人都直立起了身子,彼此挨得很近,趁对方吼叫之时,哈鲁曼的利爪从对方左脸颊上方狠狠地划了下去……而放哨的土拨鼠们显然也从未见过如此凶残的同类,全都“臣服”着,看着他走进了自己的洞穴。
晚餐是在布鲁克特那栋弥漫着浓郁松香气息的木屋子吃的。这栋木屋子旁边是畜栏,距离畜栏不远则是草料仓库,入夜时的狂风吹动着薄薄的铁皮屋顶,传来阵阵沉闷鼓点般的声音。
屋子里很昏暗,那只哈什赫鹰雕塑似的屹立于屋脚上方的一根横杆上;桌子上一堆手抓羊肉,生切洋葱圈,一碟蘸盐,还有酒——足足有六十多度,喝下去便把整个人贯穿了,而我由此看到了一个笑着的布鲁克特,随意地聊了起来。
布鲁克特是山鹰的意思,那是他出生时父亲看到的第一件事物。布鲁克特不喜欢城市,去过库尔勒和乌鲁木齐,都让他无所适从;韩炽也不喜欢,因为房子太贵;至于我,我想着的是另外的东西。我告诉他,我已经四十五岁了,布鲁克特说那是很好的年纪,而韩炽忽然问了一个傻到家的问题:布鲁克特,你感到孤独吗……然后一切就都乱了套,烈酒、抱怨、布鲁克特的神明,他试图展示多么热爱那只雄鹰,拿起了酒杯,韩炽已经醉得一塌糊涂,摆着手,他却将自己的佩刀插到桌子上,说起那些我们谁也无法听懂的胡言乱语,而无论那代表什么,我们都不会拒绝一个持刀的酒鬼,喝下了那烈酒,感到难受极了……
那时,我又在内心深处提醒自己不能和这个牧人喝第三次酒了。布鲁克特则在舞蹈,笨拙而丑陋,也完全不在乎刀的锋刃划到了什么地方,我开始同情他。又想,在他的妻子还未去世前,是如何同他度过了整整七年。
××××年11月24日 晴 雄鹰与阴影
高度白酒总是醉得快,醒得也快,没有头痛欲裂,但口干舌燥。我和韩炽离开了这辆B级房车,钻进了更宽阔也更温暖的太阳房,里面的仪器有条不紊地运行着。我想喝杯茶,可只有白开水,看着墙面上那张投影出的元素周期表(最后一种元素是money,那自然是韩炽的杰作),努力回忆着哪里还有茶叶,结果韩炽又一次打断了我。
他指着屏幕对我说,这些土拨鼠快要把地下给掏空了。
一张似伞状辐射的图案,图案以铁塔下的洞穴为中心,最长的一条线路超过了1.5千米,合计则超过6千米,而这还只是他们一整晚的“杰作”。
“如果没有计算错的话,那里应该是草料仓库。”韩炽指着最长那条线的末端说。
我们面面相觑。
于是,那天十点左右,踩着厚厚的积雪,沿着那条封冻的小河步行了大约五百米,我们叩响了布鲁克特的木门。那时,他又恢复了严肃,似乎将昨天的一切忘了个一干二净,看到我们时,没有任何尴尬。我们说明了来意,之后,一同去草料仓库查看。
此时,初升的太阳让仓库没那么昏暗,一摞摞捆扎好的方块草在仓库两边堆积着,直到屋顶,但这里的一切都整齐有序,连过道都干干净净,我们朝着最里面走去。
“这里面是什么?”韩炽指着仓库角落里一个独立的小隔间轻声问道。那隔间只有十几个平方米,四周由铁皮和铆钉固定,两扇精钢门,门上拴着铁链加一把大锁。
“没什么,矿上存的东西。”他说。
但我还是凑了上去,通过门间的缝隙,看到一些整齐码放的纸箱,纸箱上写着“乳化炸药”;另一边,透过那些巨大方块草之间的缝隙,朝里面看去,发现有几捆草垛已经散开了。
布鲁克特花了好一会儿的工夫才用叉车将外层的大草垛移开。总共有四捆草松散了,而缺少了旁边草垛的挤压,瞬间便垮塌了下来,搞得一片狼藉。
“他妈的。”布鲁克特说。
“这里有洞口。”韩炽拨开那些干草说。
“我会处理的。”布鲁克特说,他看着这些,忽然问,“这些旱獭子为什么没睡觉?”
我们什么也没有说,开始动手和他一块收拾。
“我会处理的。”布鲁克特说。
“没事。”
“这些旱獭子为什么没睡觉?”
我们还是没回应,清理着散开的枯草。
“我说,我会处理的。”他说,将一把草叉狠狠地扎进了草垛里,“他妈的,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都来了!”
收拾完时已是正午,阳光覆盖了这片冬季草场,羊群饥饿的咩咩声不断响起,布鲁克特又骑上了他的骏马,手执他的猎鹰,像个出征的战士似的策马而上,在马鞍后方则倒插一把猎枪。
那些毛色如脏雪般的羊很快就覆盖了坡顶裸露的草场,啃食草根,直到一声枪响让整个群体微微地一颤,抬起头来,意识到这枪声所激发的危险与他们无关,便又专注于草地。
之后,布鲁克特又开了第二枪,但他什么也没有打中,扫视着这片冬季草场。
我和韩炽从接近信号塔的那面缓坡小跑了过去,“布鲁克特,布鲁克特。”我喘着粗气说,“你不能打那些土拨鼠。”
他什么也没说,又朝着草线之下开了一枪,那是一只放哨的土拨鼠,子弹溅起了一些雪尘,但没有打中。“那些旱獭子,他们为什么没有睡觉。”
“布鲁克特,草料的事我们会补偿的。“韩炽说。
而这话似乎触及了一个牧人骄傲的自尊心,他又开了一枪,朝着我和韩炽的方向,如此接近,搞得我们耳朵嗡嗡作响,满面硝烟气息,之后,他就策马朝着坡顶的另一头而去。又响了几枪,根本没有打中一只土拨鼠,此时,目之所及,有三只土拨鼠正在远处直立着身体放哨,对着间或响起的枪声不再退缩。
那只哈什赫鹰便恰到好处地飞上了天空,从我们头顶无声息地翱翔而过,遮住了整个太阳,又在低空划过一道迅捷的弧线,自由、飘逸,几乎与天融为一体。
它俯冲而下,翅膀在寒冷的气流中微微地抖动着。距离我们大约一百多米,一只放哨的土拨鼠奔跑起来,朝着洞穴入口,鹰的阴影却覆盖了那里,他便折身朝另一个方向,此时,那道弧线更低了,土拨鼠放弃了奔跑,停在了枯黄的草皮之上,直立起身子,望向天空,却在鹰爪牢牢抓住他的前一秒,猛地压低身体,窜了出去。
那是一次完美躲避,但将之锁定的物种更为完美,几乎是出于本能的,这只哈什赫鹰带动气流扭过了身体,一个前跃,爪子已经牢牢抓住了他……
布鲁克特把另外两只土拨鼠扔在马下,一旁那只哈什赫鹰正在悠闲地撕开另一只的胸膛,这个牧人为此感到满意,又变得好相处起来,看着我和韩炽说,只有这样,才能让那些畜生明白一些道理。
而关于他的那些道理没什么好说的,我有些气愤,“他们只是偷了一点儿草料而已。”
“让我足足收拾了整个上午。”
“所以你就杀了他们。”我说,感觉他看我的眼神有点儿奇怪。
“这只是三只旱獭子!”他提醒我说。
我无力反驳,看了看那只进食着的鹰,正将一缕鲜红的肉吞下去,浑然不觉。
“布鲁克特,我想要另外两只,你的鹰吃不了那么多。”韩炽说。
他什么也没说,带着一点儿傲慢似的,扭过马头,继续去驱赶羊群。
我和韩炽一起回到太阳房,启动了设备,将其中一只放上了自动医疗云台。
等到剥开了第一只土拨鼠的皮毛,便发现了那些从脑干处钻出来的蓝色神经线,跟两条对称的苔线似的,位于脊椎的两侧,又在土拨鼠那浑然的双肩处散开,融入了后臂的鲜红的肌肉之中。韩炽继续操纵云台上的机械臂,横切开外层的膜胫,拨开还尚存一点儿余温的肌肉,现在,我们能看到分离的神经线正包裹在肱二头肌侧面,如另一种毛细血管似的。
“是‘无量’?”韩炽问。“无量”正是我们用于哈鲁曼和茉莉体能的基因药物,但他不该出现在哈鲁曼族群之外。
“不管他是什么,结果已经超出了预期。”我说,看着他准备打开云台上的通信同步,这样,通过那座信号塔,我们此刻的所有工作都会与总部同步。
他摁下了同步按钮,而我则关闭了云台又重启。
在云台重启的嗡嗡声中,我问他对这一切这么看。
“我认为‘无量’刺激基因完成了一次匪夷所思的进化。”
“匪夷所思,这就是你结论?你有实验样本吗?你有清晰的论证吗?有支撑论证的实验数据吗?”他想了想,开口,“这不是科幻小说,这是科学实验。”
“通过云台完成DNA过滤和分析要多久?”我问。
“分析用不了多少时间,一到两小时,DNA过滤会花些时间。”
“明天能出结果?”
“明天晚点儿应该会有。”
“等到有初步结果了再同步也不迟。你觉得呢?”
他没再尝试辩解什么,而是点点头。
××××年11月24日 晴 死鹰
现在,我正看着这只土拨鼠,即使剥掉了毛皮,却依旧可见脖颈后侧一处鹰爪所造成的创伤,这创伤恰好在一条溢出的蓝色神经线上,将其一分为二——或者说,至少在昨天夜里一分为二,但现在,更细的神经末梢扩散到了伤口内侧,围绕那处不规则的创伤,编织出一处若隐若现的微小神经网络,几乎填满了整个伤口,就像是土拨鼠大脑内泛出的另一个中枢似的——不是某种匪夷所思,只是如此切实的让人有些心跳加速罢了。
我又听到了枪声,一阵鹰啸,绵羊们怯懦的咩咩声,我不得不离开了太阳房。
那只哈什赫鹰正翱翔于蓝色亮空,仿佛具有某种神性,笼罩着整片牧场,牧羊人则立于马上,俯视着他的领地。
那只鹰再次俯冲而下,一道优美而残忍的弧线,但这一次,那只放哨的土拨鼠钻进了一处隐蔽洞穴中。那只鹰缓缓落地,收住了翅膀。一旦与大地接触,这鹰就再没那么飘逸,但威严更甚,如雕刻过猛的草原图腾似的,用敏锐的眼睛左右张望着,不曾有任何丧气之情,也让人感觉,一只鹰不可能同时失败两次。
哈鲁曼就是在那混杂而微妙的感觉中出现于我们的视野,哈什赫鹰只是闪电般的一瞥,又腾起,盘旋于铁塔上方的那一片天空。
“那是哈鲁曼,我们得阻止他。”韩炽说。
我看看丘陵顶端,布鲁克特依旧坐在马上,看着这一切。“距离太远了,等我们赶上去,说不定鹰已经开始了攻击。而且,我们又怎么去阻止一只即将发动攻击的鹰?”
“那怎么办?”韩炽问。
“把望远镜拿出来。”我说,接过望远镜的手在微微颤抖,但内心里,某种期待更甚于担忧。
此刻,那只鹰做足了悄无声息的准备,俯冲了下去;一旁,韩炽用他那人类的语言朝着铁塔下方不自禁地大喊:“快跑,哈鲁曼快跑。”
可他显然不知道谁是哈鲁曼,什么又是快跑。他直立起身子,稍稍调整了他所站的位置,用尾巴和后腿支撑,站在一片厚而密实的草地上,仰望着那只俯冲而下的巨鹰——就像一个人站在铁轨上,面对一辆轰隆而来的列车,而他却稳稳站立着,似乎有着某些不切实际的自信。巨鹰张开了自己的利爪,微微收住了翅膀,锁定了目标,在那极为致命的最后一刻,一切已不可逆转。
哈鲁曼所站立的整块草皮陷了下去,就在哈什赫鹰即将接触的一刹那,俯冲所带来的冲力则让这不足一平方米的凹陷更深,使得鹰也随之埋没,只能看到两只半张的翅膀和敏捷的头部暴露于草皮之上——它扑腾着,既狼狈又笨拙,双脚又因为没有立足点,始终无法跳脱陷坑束缚。
不仅如此,在陷坑内部似乎有什么正拉扯着它,两只半张的翅膀又陷下去一些,因而发出一声仿若悲鸣的尖啸,如此响亮、猝不及防,使得位于坡顶的布鲁克特挥动马鞭,朝着山丘下而来,可马飞奔的速度实在太快,前腿打滑,他重重地摔入了雪中,连滚带爬,从那片积雪的低洼中艰难地朝着哈什赫鹰的位置而去,中途,他停了下来,朝着天空开了一枪,又开始艰难地奔跑于雪中,期间摔倒了好几次。
等他赶到那处陷坑,连巨鹰骄傲的头颅也不见了踪迹。
他将猎枪放在一边,半个身子探入陷坑,之后,脱掉皮手套,开始用手挖了起来。
一切如此急转直下,我们愣了好一会儿。韩炽朝着那个位置而去,但我拦住了他,指指铁塔,那下方我们安装的监控装置距离布鲁克特不足三十米。在监控下,是哈鲁曼,即使无法看到那背部的V字标记,但我知道那就是哈鲁曼,精瘦,直立着身体,左手握着一片鹰的尾羽,放在胸前,像野性十足的印第安人。在那高低起伏的冬季草场或称之为土拨鼠的领地上,所有从冬眠中醒来土拨鼠家族都钻出了自己的洞穴,大约有四十到五十只,全都注视着通信铁塔下的哈鲁曼,压低着身体。
“相信我,现在可不是好时候。”我拦住韩炽说。
此时,慌乱的布鲁克特从那约半米深的陷坑里爬了出来,没有意识到那些出洞的土拨鼠,也没有向我们求助,而是呼唤着自己的马匹,朝着自己木屋的位置飞奔。大约十来分钟后,他又回来了,带着铲子和一把短柄锄头,开始疯狂地挖掘起来……
阳光没有了,寒冷毫无过渡地又来了,丘陵顶刮起风,冷酷得像刀子,那些羊也开始咩咩地叫了起来。布鲁克特从那堆挖得乱七八糟的土堆中爬了出来,回到丘陵顶,开始驱赶那些羊回到底部的畜栏里。
我远远地看着他,这个在日暮时分已一无所有的牧羊人,觉得应该和他聊聊,又觉得现在不是时候,因为我又想,他此刻并非一无所有,还剩大把大把无处发泄的愤怒。
太阳房外的风越刮越大,似乎另一场暴风雪就快要来临了。等到那些颗粒状的雪随风剐蹭着房屋外壁时,分离机停止了工作,将过滤的DNA送入了检测系统,十几分钟的预热之后,在电子显微镜的屏幕里,我们看到了那种东西——“无量”所作用的标靶基因不见了,但这一整套提取和分离策略都是为检测“无量”而设计的,屏幕里是一些杆状菌群似的存在,长度在0.5至0.8纳米之间,长满鞭毛,在基质原液中不断游动着,相互融合、分裂,仿佛一场我们尚且理解不了的微观战争。
所以这要么涉及复杂的进化机制,要么就与“无量”完全无关。但哈鲁曼及周边族群神经系统如喷泉似的进化却是事实,这种进化不必通过漫长的子代变异,似乎具有某种“传染性”,神经系统会由脑干中溢出,由脊椎两侧延伸,似两条分明、对称的苔线,首先在肱二头肌处缠结,似乎在形成一个次级大脑似的——而这就是我们如今唯一知道的,至于这种进化是否让这些啮齿动物更聪明,我想,这世上还没有哪种啮齿动物能制作出捕鹰陷阱,而这还远非他们的极限。
“你怎么看?”我问韩炽。
“我觉得应该报告总部。”他说,看着我。
现在,这些又回到了老路子上,我得承认这个新手搞得我有些焦头烂额,他根本不会明白,这里不过只有一只鹰而已,而在公司,每一个人都是“鹰”,随时准备抢夺别人的成果。但我没和这个年轻人聊这些,而是聊一些他那个年龄相信的事情,例如科学精神、实证主义,让他认为我们的等待是有意义的,而这花去了比实验本身更多的时间,但他似乎并不买账。
“我还是觉得应该报告总部。”
我看着他,没心思再说点儿什么,并非因为忽然丧失了耐心,而是眼前的屏幕里有了异常。屏幕连接着铁塔下的远红外摄像头,拍到了布鲁克特那辆老掉牙的皮卡车,两束车前灯摇晃着,来到了铁塔下方,他下了车,狂风中,他摇摇晃晃,腰间则别着那把镶嵌着宝石的精美腰刀,似乎刚刚喝过酒,从车上举下一只大约一米多高的铁皮桶,狂风刮来差点儿让他跌倒,但他稳住了,双手提桶,蹒跚而行,来到铁塔下方的哈鲁曼家族洞口,将里面的液体倒了进去,一些溅到了他那件长长的羊皮袄子上,于是,他不得不脱了那件外套,挂在皮卡车的另一侧,然后擦亮一个防风火炬,扔进了洞口。
一股耀眼的火舌从洞中蹿起,几乎晃白了整个屏幕,渐渐微弱下来。布鲁克特绕过车,穿上那件羊皮袄,朝着熄灭的洞口吐了一口唾沫。忽然,三个滚滚燃烧的火球从距离不远的两处洞口中钻出,朝他扑来,将他扑倒在地。他在地上慌乱地挣扎,拍打着被点燃的衣摆,直到熄灭,那三个火球也寂静了下去。他站起来,看了看还在抽搐的土拨鼠尸体,又吐了一口唾沫,之后,上了皮卡。
等到我们赶到时,两束车灯已在远处,在寒风和刺肤的雪颗粒中孤独摇晃着。然而即使这风不断,依旧吹不散那股肉体被烧焦的气息,以及一片漆黑,在这漆黑中有什么闪着微弱的红光,我打开电筒朝那里走去——是茉莉,哈鲁曼最先醒来的妻子,右后肢的追踪器正不断地闪着红光,所有的毛都被烧光了,裸露出暗红色的皮肤、岛屿似的烧伤。
“他死了,他们都死了。”
我的心沉了下去,但还是弯下腰,把茉莉装进了一只盒子里,作为实验样本。接着寻找另外几只烧死的土拨鼠,但周围一片黑茫茫的,我们打着强光电筒也什么都没找到。
“得找到哈鲁曼。”我说,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你去看追踪器,顺便把那只动力昆虫也拿来。”
“我认为应该先去找布鲁克特。”韩炽说。
“什么是他妈的我认为!去把动力昆虫拿来。”我对着他大吼道,然而一阵刮过的冷风让我马上冷静了下来,“没用的,那鹰对他太重要了,而且烧都烧了。”
那时,我猜他有些不情愿吧!他站在黑暗中好一会儿才离开,我一个人在通信铁塔下,周围只有凌乱的风声,忽然又停止,静得跟片墓地似的,我忍耐着,等到那些愤怒不再那么强烈,才开始活动僵硬的身体。没过多久,韩炽来了,提着一只铝合金外壳的小盒子。
“我看了,哈鲁曼还在下面,不知道是死是活。”
“干得好,把动力昆虫放下去。”我说,看着他小心翼翼地拿出那比指甲盖大不了多少的金属昆虫,以及一块便携屏幕。
调试花了一些时间,韩炽启动了昆虫,逆着风,飞进了洞穴。
洞壁已经被烧得焦黑,在临时洞内,有一只土拨鼠已经蜷缩成一团,被烧得皮开肉绽。动力昆虫扫视了一番,收起了金属翅膀,开始缓慢地爬行起来,来到隐蔽在洞壁口内侧的远红外摄像头前,拨开了阻挡镜头的土颗粒,接着,往更深处。另外两个摄像头则没那么幸运,已经完全烧坏了。而在冬眠洞口对面,另一个更宽的洞口深入到地下,那便是哈鲁曼最初朝着地底挖掘之处,韩炽指挥动力昆虫爬了进去。
爬行了一会儿,摄像头便一片白茫茫的,直到自动修改了红外参数,才适应这黑暗洞道内溢出的微光。随着光越来越亮,一个宽阔、方正的洞穴出现在屏幕里,洞穴有半米来高,地面平整、干净,弧形的墙壁黑乎乎的,一直延伸到微弱光线照不到的地方;光源则来自另一边,几只蜷缩着身体的土拨鼠出现在屏幕里,御寒的皮毛烧得一干二净,裸露出暗红色的皮肤,其中一只尾巴烧得焦黑,像一截木炭。他们剧烈地颤抖着,或许是因为此刻的痛苦,也或许是记忆中的。
现在,已经能看到那堆火,不是汽油的余烬,而是一堆由枯草、细枝所堆积起来的小小篝火,距离篝火最近的是哈鲁曼和另外两只被火焰剥夺了御寒皮毛的土拨鼠,形容枯槁,眼中反射着火焰,但他们显然比其他同类先克服了对这种事物的恐惧,不仅离火更近,还不断将细枝和枯草扔进火堆里,那火因此更旺了,闪烁着。
愈发旺盛的火使得两只受伤的土拨鼠颤抖得更厉害,朝后退回了黑暗与寒冷之中。“复杂”的安静持续了好一会儿,有同类开始学着哈鲁曼,直立起身体,离火更近,依靠火堆取暖,第二只也站了起来,接着是第三只……同时,开始学着哈努曼,将身边能找到的枯草和漆黑的细枝扔进去,其中一只则捡起了那只价值三十多万的动力昆虫,也扔了进去。

刊登于《科幻世界》2020年11期
最热文章

完美人生

隐形时代(下)(1)

隐形时代(上)(1)

【榕哥烙科】第537期:进化的速溶咖啡,如何越来越醇?

“瓷韵中秋,科技添彩”——2024年中国科技馆陶瓷主题中秋专场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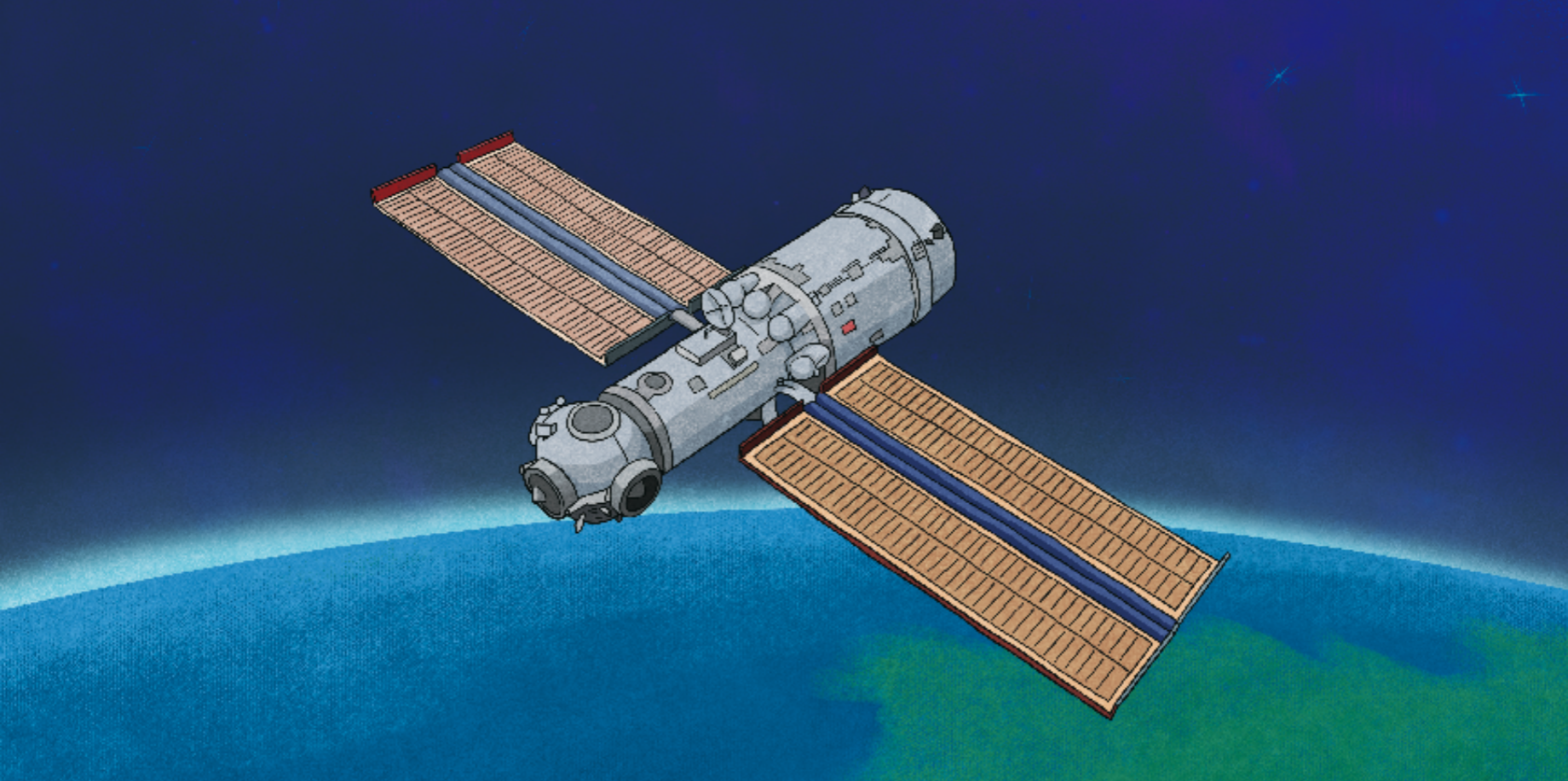
守时大神——空间冷原子钟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977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977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