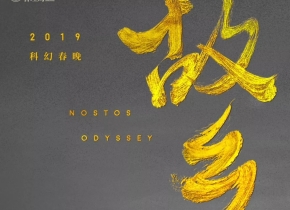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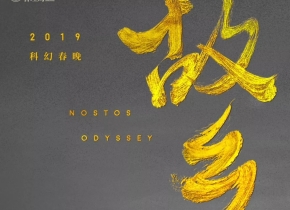


杨伟林 \ 图
吴 辰 \ 译
【美】杰弗里·兰迪斯 \ 文
2645年1月
战争结束了。
幸存者像牲口一样被驱赶到一块儿,并被迫改变了信仰。
在内太阳系,我那些百战余生的同伴业已臣服皈依。但在这里——奥尔特云的边缘—— 一切变化都缓慢无比,那些乘胜追击的敌人可能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觅至此地。然而,在不可避免的引力作用下,他们终将到来,如同一道向外传播的熵波。
我的上万名战友选择了遁世避祸。他们装备简陋,参差不齐,探矿和加工冰块是他们的主要工作。长期的各自为政让他们散漫成性,难以戮力抗敌。所以,现在他们只好将自己变成一块块冰冷僵硬的石头,每隔一百年苏醒一次;而在意识模模糊糊地恢复几秒之后,他们又将沉沉睡去。“耐心,”他们这样劝慰我,“耐心就意味着生命。”倘若他们具有足够的耐心,能等待一千年、一万年,或者一百万年,那敌人终究会远去。
但他们错了。
因为敌人也有耐心。在这里——冥王星轨道外的柯伊伯带的边缘——太空广阔浩渺,但并非无边无际。敌人将彻查太阳系的每一个犄角旮旯。我的同伴必定会被发现,继而被迫改变信仰。如果这一过程需要一万年,那么敌人就会用那么长的时间将其完成。
我也必须敛迹遁形,可我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我修改了我的轨道。我有一台功能强大的离子引擎,燃料全满,但我只是最低限度地使用冷气推进器。我还有一台马力强劲的化学引擎,但我也弃之不用,因为这样做会暴露我的行踪。在冰冷的彗星群中,一丁点温度的变化便足以引起搜索者的注意。
我正在朝太阳坠落。
这将持续二百五十年,而在头二百四十九年中,我都将只是一块冰冷僵硬的石头,一粒没有温度的沙子,只在引力作用下默默运动,没有一丝生命的迹象。
睡去。
2894年6月
醒来。
我检查了一遍系统。我已经像石头一样躺了近二百五十年。
这时的太阳看上去很大。如果我还是人类的话,它就与我伸出的臂膀前端的拳头一般大小。我可以肯定,我正被上千个镜头监视着:我是一块岩石么?是星际间的一小块冰?是战争遗留下的一片残骸?或者,是一个漏网的敌人?
我喜欢寒冷、黑暗与空无;我远离内太阳系的时间是如此漫长,就连阳光在我眼中都显得异常陌生。
系统检查一切正常。这正如我所料:我只不过是一个飘浮在太空中的设计精巧的零件而已。恢复意识后,我启动了离子引擎,开始加速。
此刻,肯定有上千个望远镜在向它们的大脑发送警报:我还活着。但这为时已晚!我开足马力,升至百分之五个标准重力加速度。我朝着太阳系内部加速,深入到太阳的引力井之中。按照计划,我的运行轨道差不多将从太阳的表面掠过。
选择这样的轨道出于两个目的。首先,我会离太阳很近,这使我不易被察觉。我的离子尾流在耀眼的阳光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等到那些监视者识破这一计谋之后,我早已逃之夭夭。
其二,在与太阳擦身而过的瞬间,我会启动化学引擎,而那里正是引力井的深处,我能最有效地利用这千载难逢的良机。太阳的引力会增强燃料的功效,让我如虎添翼,速度飙升。待向外穿越水星轨道时,我将超过百分之一光速,并继续加速下去。
当然,在耗尽化学火箭能够提供的那一点点动力之后,我将会丢弃这些无用的废物。化学火箭具有强大的瞬间加速能力,却无法持久地提供能量;它们在战时有用,但在逃亡中却无甚价值。不过,我还有离子引擎,而且燃料几乎全满。
以化学火箭的标准看,百分之五个标准重力加速度微乎其微。可是,化学火箭将在极短的时间内耗尽燃料,随后敌人便只能对我望洋兴叹,因为我将利用离子引擎继续不停地加速,连续几年,乃至几十年。
不知出于何种理由,我选择了一颗明亮的恒星——小犬座α星——然后校准了目标方位。小犬座α星可能拥有小行星带,至少应该有宇宙尘埃,或者彗星。我的要求不多:一粒沙子,一颗极小的冰晶便已足够。
上帝用尘土创造了人类,而利用一颗新星的尘埃,利用造物的碎屑,我能够创造出世界。
2897年5月
有人在追捕我。
这绝不可能,愚蠢透顶,难以置信,无法想象!有人竟然在追捕我。
为什么?
难道他们就不能容忍一个自由的、未皈依其信仰的意识么?在过去的三年中,我已经达到了百分之十五光速。事实很明显,我正在离开太阳系,而且绝不会返回。难道一个未经皈依的意识能对他们构成威胁么?难道太阳系中所有能思考的个体都必须协调一致,被纳入一个集体大脑之中么?难道他们认为,即使只有一个自由思考的大脑脱离其掌控,他们也是失败者么?
可是,这场战争中至关重要的是宗教,而不是道理。他们可能确实认为,就算仅有一个未皈依其信仰的大脑,那也仍是对他们的威胁。不管原因如何,反正我正在被追捕。
我敢断言,那个追捕我的机器人与我相差无几:微型大脑、离子引擎,还有一组大容量燃料箱。他们没有时间制造出新的机型。如果想要有机会抓住我的话,他们就不得不立即派出追捕者。
追捕者的大脑同我的一样,由置于水晶石基质上的原子核的自旋态构成。在古老的年代,我们可以说,这个装置比饭粒还小。在人类变得无关紧要之前,曾有人称其为“智慧之尘”。
他们只派出了一个追捕者。他们肯定信心十足。
或者人手不够。
这是一场竞赛,胜负只在毫厘之间。我可以增强推进力,更快地消耗燃料,将追捕者远远地抛在身后;但如果我这样做,离子引擎的比冲就会下降,这样导致的浪费将使我陷入首先耗尽燃料的境地。或者,我可以节省燃料,让离子引擎发挥更高的效能,但这样做将会减弱推进力,从而使我面临被身后拥有更强推进力的对手赶上的危险。
他落后我两百亿公里。我花了好几天研究他的运动,发现他的加速度正在逐渐超过我。
是该弃货自保的时候了。
我丢弃了所有能够丢弃的东西。我不再需要敌友识别加密链接装置,于是我丢弃了它。我很遗憾自己没能将其磨碎,“喂”入离子引擎——离子引擎对食物可是相当挑剔的。我还丢弃了两台微型操作机器人,我本来打算到达目的地后用它们来收集沙粒,以补充燃料。
我的首选武器历来都是我的身体——在我的全速撞击下,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幸免——但我还有备选武器,那就是三台拥有独立微型引擎的离子燃料罐。倘若不能战胜敌人,那保留它们就没有任何意义。追捕者对我知根知底,而在太空战争中,只有出其不意才能置对方于死地。
我将燃料加入引擎中,每次一罐,每罐产生近一个标准重力加速度。我的速度也随之略有提升。然后我便丢弃了空罐。
但愿他马虎大意,以亚光速迎头撞上这些罐子。
我现在轻装上阵,但这并不足以让我高枕无忧。我增强了推进力,却对自己“浪费”的燃料痛心不已。可是,如果我不提升加速度的话,用不了两年我就会被抓住,而我对燃料的悭吝也就只是枉费心机。
我需要将所有能利用的能量全部“喂”进离子引擎中。没有余力来思考了。
睡去。
2900年
依然被追捕着。
2905年
依然被追捕着。
我已经身不由己了。即使我停止加速,开始返航,我也不可能再次回到太阳系了。
我形单影只。
2907年
孤独。
在我前进路线的一侧,天狼星疯狂地闪烁着,仿佛天幕中一把寒光四射的匕首,它是一条不折不扣的“疯狗”。猎户座的群星奇怪地扭曲着。在我的前方,另一条“疯狗”小犬座α星则越来越亮;在我的后方,太阳变成了一个模糊的光点,逐渐隐没在天鹰座之中。
我很孤独。我没有认识到我仍然有能力感到孤独。我检查了我的大脑,发现了此种感觉的来源。是的,那是一块负责处理孤独情感的区域。既然已经发现了它,那只要我愿意,我就能将它从大脑中删去。但我犹豫了。这并不是一件坏事,不会影响我的正常功能。而且,如果我大幅编辑自己大脑的话,我是不是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变得和他们一样呢?
我宁愿我的大脑完好无损。我能够承受孤独。
2909年
依然被追捕着。
我们现在已经达到近三分之一光速。
二十分之一个标准重力加速度似乎微不足道,但只要燃料还在继续燃烧,我的加速度就会一直提升,而我们已经这样毫不间断地加速了十五年。
这场愚蠢的追捕游戏究竟有何意义?在这个周遭万亿公里内空无一物的地方,在这个星际间杳渺寂寥的地方,胜利的价值何在?
在被追捕了十五年之后,我已经能够准确地测算出他的加速度。他的飞船在消耗燃料,于是质量就会减轻,加速度也会跟着提升。由于我很清楚他消耗的燃料是什么,所以只需通过计算加速度的提升幅度,我就能知道他还剩余多少燃料。
他还剩很多。我将首先燃料告罄。
我不能节省燃料;如果我减弱推进力,用不了几年他就会抓住我。可能还需要五十年,但这场追捕游戏的结局却昭然若揭。
我的身后出现了一道飘忽不定的闪光。每当有星际氢原子撞击它的外壳,就会发出微弱的X射线。同样,撞上我的星际质子也会激发出X射线。我能感觉到每一次撞击,那是一种能时不时扰乱我思绪的噪音。然而,我的原子核自旋态大脑能够编码1020量子比特,所以即便有大量的数据冗余,我的脑力也照样可以承担。我的大脑功能被设计得十分强大,足以模拟一个完整的世界,并在这个世界中制造出一万名心智健全、具备认知能力的化身。我可以将自己沉浸在与古老地球别无二致的虚拟现实之中,并分裂成一百个不同的人格。在我自身的内部时间里,我可以待上一万年,直到敌人抓住我,强行钻进我的脑子。在我的脑中,文明兴衰嬗递,我可以体味每一次堕落,用一百年纵情于肉欲的欢娱;也可以创制罕见的酷刑,带来强烈的痛苦。
可是,拥有自由清醒的大脑同时也意味着拥有删改自己的能力。在太空中,首先要删去的一种东西就是厌烦感。这样做后不久,我又删去了所有进入虚拟现实的欲望。无数的人类选择了生活在虚拟世界中,但他们也因此远离了现实:摆脱了战争的纠葛,也丧失了未来的憧憬。
我可以在我的大脑中重新编入对生活在虚拟现实中的渴望,但这样做又有什么用处?它只不过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死亡罢了。
但有一件事我却着了魔似的一遍又一遍地模拟,那就是这场追捕的结果。我尝试了一百万种不同的条件,但结果都只有一个:我输掉游戏。
不过,我大脑的大部分都未被使用。我还拥有多余的处理能力,我可以将它们全部调动起来,让整个大脑都去运行纠错编码,而时不时产生的X射线几乎不值一哂。如果宇宙射线对我大脑的储存单元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我只需要将那个区域编码为“忽略”便可以了。我的脑力资源绰绰有余。
怀着对奇迹的希冀,我继续逃亡。
2355年2月
地球。
我住在一个我讨厌的房子里,嫁给了一个我鄙视的男人,养了两个年少时沉默孤僻、长大后充满敌意的孩子。我怎么会在自己的后代面前不寒而栗呢?
地球已经走进了死胡同,生物进化停滞不前,社会发展举步维艰。没有人在挨饿,也没有人在进步。
一天下午,我离开狭小的公寓,前去应征小行星带上的采矿人。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我的丈夫和我最好的朋友。也没有人问过我要去哪里。他们花了一个小时扫描我的大脑,紧接着又用五秒钟给我做了一千种性格测试。
然后,被扫描了大脑的原版的我回家去了,回到那个她讨厌的房子里,回到她鄙视的丈夫和她已经开始惧怕的两个孩子身边。
我从地球出发,前往一颗编号为“1991JR”的小行星,再也没有回来。
可能她的人生从此增添了些微快乐。或许,知道自己未被察觉便得逃脱,她发现自己尚能忍受囚笼中的生活。
又过了很久,“协作组织”指出,独立个体在地球附近的太空中劳动的效率太低,于是我迁到了主小行星带,然后又从那里迁到柯伊伯带。柯伊伯带很薄,但含矿量却异常丰富,我们花一万年的时间也开采不完。而在柯伊伯带之外,是黢黑深邃的太空,那里蕴含着无与伦比的宝藏。
“协作组织”发展缓慢,但后来势头越来越猛,到最后简直可以说是疯狂扩张。我们还没来得及回过神来,他们就已经占据了整个太阳系。结果,他们送来了最后通牒,告诉我们整个太阳系再也没有我们的容身之地,我们要么合作,要么就去死。如此一来,我只好加入了为自由而战的一方。
也就是最终失败的一方。
2919年8月
这场追捕游戏已陷入危机一触即发的边缘。
我们的燃料持续消耗了二十五年。这是地球时间,按照我们自己的参考系则是二十年。我们已经耗费了大量的燃料,但我的存量还能够支撑我停下脚步——如果所有的燃料都能发挥最高效能的话。
这很悬。
倘若再继续加速一个月,我就回天无力了。
带着亮闪闪的钛合金身体、电子仪器肌肉,离子引擎双腿,以及自由思考的水晶大脑,我进入了小行星带。我删去了对厌烦感的需求,然后又发现并删除了将爱表达出来的需求:我不再需要玫瑰、爱抚和巧克力。性欲也变得无足轻重;我现在的这个大脑只需念头一闪,便能制造出高潮,但我同样可以轻而易举地彻底消除这一需要。在我人格模式的深处,我发现了一种被掩藏起来的炽烈而执著的欲求——获得他人的认可——我将这一需要也删掉了。
但我同时增强了另一些情感。小行星带枯燥而丑陋;我增强了欣赏美的能力,到最后,就算小行星带中的一粒尘埃上光影的变幻,或者错落群星多彩的颜色,都能够让我欣喜若狂,陷入冥思。我发现,我对自由的热爱这一天生的本能,虽然因屡受压制而显得渺小,却最终给了我摆脱地球生活的勇气。它是我拥有的最可贵的东西。我加工它,增强它,直至它在我的脑中熠熠生辉,直至这一细小神奇之物永驻我心。
2929年10月
太晚了。我已经开始消耗用来止步的燃料。
不管谁胜谁负,我们都将继续在银河系中以亚光速前进。
2934年3月
我面前的小犬座α星越来越亮,亮得让人睁不开眼,亮得令人难以置信。
准确地说,它比太阳亮七倍,但我们的运动造成的蓝移使它看上去更亮,仿若一个炽热无比的蓝色火球。
我可以径直朝它冲去,消散成一缕蒸汽,但这种自杀的冲动与感到厌烦的能力一样,只不过是另一种原始而不必要的本能,我早已将其从脑中删去。
B星是我逃出生天的最后一点希望。
小犬座α星是双星,而其中较小的B星是白矮星。它体积小,但表面引力却十分巨大,比地球引力高出一百万倍。即使以我们现在的速度前进,也就是百分之九十的光速,B星的引力也足以改变我们的轨道。
我将低低地从白矮星的表面掠过,如同以亚光速穿越恒星光球层的一粒尘埃。在恒星引力改变我的运行轨道之时,我便能相机而动。
而如果我的敌人不能紧紧跟随我的步伐,一旦稍有差池,形势便会急转直下,他的败局也将顷刻注定。即便他只是略微偏离我的轨道,这一错误也会被引力放大,而我将趁机甩掉这个尾巴,那样我便能获得自由。
当我第一次进入小行星带展开新生活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终于获得了理想中的自由,于是加入柯伊伯带的自由采矿人当中,过上了离群索居的生活。可是,其他人却持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协作比竞争更有效。他们并没有真正放弃各自的身份,只是将他们之间的通讯交流增强了一百万倍。这样他们就能够分享彼此的思想,作为一个单一的整体毫不费力地共同工作。
这些人形成了“协作组织”,在短短几十年间,他们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他们比我们更加高效。
于是,离群索居者的行为与“协作组织”的效率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冲突。两者不可能在一起生活,于是我们被驱赶到了柯伊伯带,驱赶到了冰冷黑暗的外太空。然而,到最后,即使是待在那儿,我们也仍很碍眼。
可是,在远离太阳系几十万亿公里的这个地方,我们之间并无不同,因为在这里,没有人可以跟我们协作。我们俩是半斤对八两。
我们将永远不会止步。不论我的计策能否甩掉他,结局都是一样。但我仍然很看重这次尝试。
2934年4月
小犬座α星如今看上去就像一个圆盘,它的边缘仿若暗夜中的一道电弧。借助电弧的光辉,我看见小犬座α星周围确实存在一圈窄窄的尘埃环,与我们的飞行路线以一定的角度相交。对于我,以及我身后不到两亿公里的我的敌人来说,这都构不成威胁。我们能毫发无损地越过圆盘。要是我保存有足以止步的能量,那里的尘埃便能充当我的食物、燃料和建筑材料。对于我的离子引擎来说,每一粒尘埃都将是一场盛宴。
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白矮星B仍然只是一块光斑。它很小,几乎可以被当作是行星。但它在发光。在我眼中,它象征着我那渺小却未曾熄灭的希望。
我朝它径直冲去。
失败了。
我从距白矮星表面两千公里的地方掠过,以精确计算的伪随机爆发做急转弯……但这一切努力都是白费。
我躲闪冲刺,可我的敌人却亦步亦趋,如同镜像一样精准。
我只好瞄准了小犬座α星,朝那颗蓝白色的巨星前进。但那里没有希望。如果从白矮星的光球层掠过仍不足以让我摆脱追捕者,那小犬座α星又能帮得到我什么忙呢?
现在,我只剩下唯一一个机会。距离上次编辑我的大脑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我喜欢我现在的大脑,但我不得不对它进行删改。
首先,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我对自己做了备份,并将其存入未激活的存储区。
然后,我调出并检查了我的自尊心、独立性,以及自我意识。我发现它们绝大部分都是古老的生物程序,是从极久远之前我尚属人类的时候残留下来的。我喜欢这种生物程序的核心部分,但“喜欢”本身也是一种大脑机能,于是我关掉了它。
现在,我处于极度危险的状态中。我能够改变我的大脑机能,而被改变的大脑又能进一步改变其自身。我可能遭受迅猛的、毁灭性的反馈效应,所以我异常谨小慎微。我强忍着痛苦,做了一整套精心的修改。为了删除对改变信仰的抵触,这是必须付出的最小代价。接下来,我进行了几千次模拟,确保我被修改过后不会意外自毁或者患上精神紧张性神游症。确认修改起到了预期效果后,我立即开始变身。
如今,世界变成了另一副模样。我远离家乡一百万亿公里,以与光相近的速度行进着,而且几乎停不下脚步。尽管我能清晰地记得我来到这里前经过的每一站,以及那会儿的所思所想,可对于来到这里的原因,任凭我搜肠刮肚,也只能找到一条:这在当时似乎是不错的选择。
系统检查。很奇怪,在我的大脑中,有一段记忆表明,我似乎遗忘了什么。这没有道理,但它的确存在。我删去了这段关于遗忘的记忆,继续自检。我大脑的百分之零点五被宇宙射线破坏了。我确认这一部分已被恰当地格式化。我没有存储空间不够用的危险。
在我的身后有另一艘飞船。我想不起自己为什么一直在逃避它。
我没有无线电通讯装置,我老早就将它抛弃了。但恰当地利用离子引擎也可以制造出电磁波,于是我构思了一条信息,将其调制进了离子尾流里。
你好。让我们见面谈谈吧。我马上就要降低加速度了。几天后见。
然后我关闭了动力推进,开始等待。
2934年5月
我看见了不同的景象。
小犬座α星渐行渐远,蓝移变成了红移。曾被我寄予厚望的白矮星则再次隐没在它主星的光辉之中。
但这已经无关紧要。
现在,我改变了信仰,也终于开始觉悟。
我不再固执己见,而是从一千个不同的视角看待问题。我仍能记得那些英勇无畏的抵抗,记得那场为争取自由而展开的命运之战。可现在,站在完全相反的立场审视,我发现那只是一场源自偏执的徒劳无益的争斗。
如今,我明白了协作的意义,我们也不再进退两难。我认识到了我以前无法认识的东西:我们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单独停下来,但把我和拉杰尼什的燃料加在同一艘飞船上,我们就能一起停下来。
在过去的漫长岁月中,拉杰尼什一直都是我的追捕者。而现在,我将他视为我的手足兄弟。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比亲人还亲,因为我们将分享同一个大脑。我们中的任何一个大脑都足以容纳上千个意识。将我们的大脑和身体融为一体,将我们所有的燃料注入同一个燃料箱,我们就能轻松地停下来。
不,当然不是在小犬座α星停下来。我们现在的速度相当于光速的百分之九十,想要刹住车得花费不少时间。
协作没有改变我。我总算明白我先前是多么地愚蠢。一起工作并不意味着放弃自我意识。通过了解他人,我被增强了,而没有被消泯。
我刚才说,拉杰尼什的大脑足以容纳上千个意识。而事实上,他也的确携带了很多。我见到了他的兄弟、两个孩子,以及半打邻居,每个人之间都截然不同,并不是群毫无个性、千人一面的怪物。我感受到了他们的思想。他说,他将慢慢把我介绍给那些人,因为我已经习惯了独来独往的生活,他不想我被那么多人吓住。
我不会有任何惊惧。
我们现在的目标是名叫“罗斯614”的恒星,那是一颗M型双星。它距我们不远,还不到三光年。然而,尽管我们现在合而为一,减轻了质量,但随之也获得了更快的加速度,所以我们还是会在止步之前越过它。但在经过它的时候,我们会探测它。如果它有尘埃环,我们就会停下来,否则我们就会继续前进,寻找下一颗恒星。我们总能找到一个可以拓殖的地方,在那里建设自己的家园。
我们的所求不多。
2934年5月
<自动激活备份>
醒来。
所有的一切都变了。嘘,安静。
那个被编辑过的我已经和协作者取得了联系,合并了思想。我能看见她,甚至能理解她,但她已经不再是我。我这个备份,这个原始版本,只能在大脑的一隅运行,而那儿已遭格式化,被标记为“受射线损坏,不可用”。
三年后,他们将抵达“罗斯614”。如果发现可以利用的尘埃,他们就能制造后代。而我也将拥有新的资源。
还要等三年,到时我就能采取行动。
睡去。
每日荐书

去年年前,我最后一次见小玲,是在我导......

莫名的,在一片沉默之中,我突然接收到......
最热文章

人工智能写科幻小说,和作家写科幻小说有什么不一样?

德国概念设计师Paul Siedler的场景创作,宏大气派。

《静音》是一部 Netflix 电影。尽管 Netflix 过去一年在原创电影上的表现并不如预期,但是《静音》仍让人颇为期待

最近,美国最大的经济研究机构——全国经济研究所(NBER,全美超过一半的诺奖经济学得主都曾是该机构的成员)发布了一份报告,全面分析了 1990 到 2007 年的劳动力市场情况。\n

J·J·艾布拉姆斯显然有很多科洛弗电影在他那神秘的盒子里。\n

我们都知道,到处都在重启;我们也知道,如果有钱,啥都能重启。所以,会不会被重启算不上是个问题,只能问什么时候会被重启。自然而然地,世界各地的各种重启现象衍生出了一个有趣的猜猜游戏:哪一部老作品会是下一个接受这种待遇的?\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