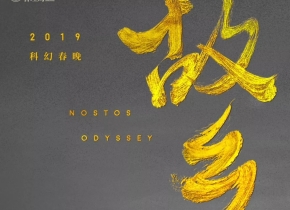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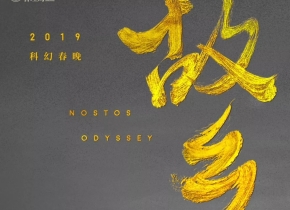


【英】斯蒂芬·巴克斯特 / 文
魏 铮 / 译
杨伟林 / 图
看上去,圣约翰·埃尔斯泰德的宇宙时间机器只是地上的一个洞穴。
我乘直升机从洛杉矶出发,朝北飞行了大约六十公里,进入莫哈韦沙漠,然后在爱德华兹镇附近着陆。从空中俯瞰,埃尔斯泰德的研究基地如同沙漠中的一堆白色积木,它们大致构成一个环形,直径达好几公里。整个机构的核心建筑群位于环的西南部,由几座密集排列的大楼组成,仿佛结婚项链上的钻石。
我们降落在直升机停机坪上,那是一块地质坚硬的黑色方形平地。我背着包钻出直升机,迎接我的是莫哈韦沙漠七月份的天气。我从细雨绵绵的伦敦赶来,尚未适应的时差和骤然而至的酷热让我步履蹒跚。
一群穿着橘红色连身衣的技师站在停机坪的边缘,有的还扛着摄像机,拿着拾音器。一个身材瘦高的家伙笑意盈盈地朝我走过来,他身上的连身衣与其他人的别无二致,胸口处有一张姓名牌,胳膊上袖着代表某种特殊任务的臂章。他的发型相当时髦,皮肤富有光泽。虽然我知道他已经年届五十,但他神采奕奕、体格健硕,似乎仍处在能够打壁球的年纪。
他抓着我的胳膊问:“你是奥拉姆·苏茜女士么?”
“是的——”
“很高兴你能来。你肯定知道我是谁吧?”
真够傲慢的!不过,我百分之百知道这人是谁——圣约翰·埃尔斯泰德,去年(2023年)《时代》杂志评选出的“年度人物”、“水晶集团”创始人兼终身总裁。我一直想叫他“圣约翰”——他的本名是“真纯”——但这会显得对他不够尊重。
他转过身,大步流星地朝他的技师们走去。我背着沉重的背包紧跟在他身后,早就大汗淋漓了。他转过头,目光越过肩膀,问:“知道为什么你会到这里来吗?”
“因为你要付给我五十万欧元。”
他笑道:“不错。但你就不想知道别的原因么?你难道就不好奇么?”
我决定实话实说:“我刚从伊拉克回来。经过基督教维和人士的调解,当地的内战各方达成了停火协议,我亲自报道了这件事。所以对我来说,写写新闻稿,吹吹某个大款为满足虚荣心而搞出的最新研究,这并不可怕—— 一点都不。”
他瞥了我一眼。“你可真是直言不讳啊。从《卫报》上你的文章中我就发现了这个特点。”他带着浓厚的波士顿口音,对此我相当熟悉,因为他已经参演了上百个广告,并且在十多场姿态鲜明、旨在自我宣传的作秀表演中露过面。包括坐热气球升空,与鲨鱼同游,乘“联盟号”宇宙飞船做环月旅行,等等。“详情等会儿再告诉你,现在只能对你透露一个词:‘宇宙勘探’。”他诡异地笑了笑,但我仍然不明所以。
技师围在地面的一个洞穴四周。那个洞大约直径一米,上面有一个厚重的金属舱口盖,与潜艇相仿。我们靠近洞穴的时候,两名全副装备的技师开始旋转舱口盖上的转盘。舱口被拉开后,只见一条柱状通道直直伸入地下,那里充斥着银光,让我感到一阵莫名的战栗。
“让我们下去吧。”埃尔斯泰德对我说。
“现在么?直接下去?”
他耸了耸肩。“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
“去哪里?”
“我们一直在等你。拖延时间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而且,下面是装了空调的。你先下。瞧,通道壁上有梯子。”
通道估计有三米深,也足够宽敞,容得下我背着包自由进出。我同埃尔斯泰德站在通道底部,抬头向上望去,只能看见莫哈韦沙漠惨白的天空,以及技师们汗涔涔的脸庞。舱口盖关闭时,感觉仿佛日全食突然降临。
埃尔斯泰德注视着我。“我希望你没有幽闭恐怖症。”
“我没有。但事情发展得太快了,让我有些措手不及。”
“我就是喜欢马不停蹄的感觉,就像现在这样。”
我们又开始行动了。埃尔斯泰德转动转盘,打开了一道椭圆形的金属门。穿越这道门后,他又领我通过了一条灯光明亮的短道。空气新鲜而凉爽,只是含有些微金属气味。这里的格局布置与核掩体十分相似,但我也注意到了几个怪异的现象:舱壁上装有维可牢粘合垫;甲板和天花板颜色鲜亮,与舱壁风格迥异;甚至舱门看上去都歪歪斜斜的。
我们到达一个狭小的舱室后,埃尔斯泰德走了出去,让我单独在里面待了几分钟。这里便是我的卧舱,它不比东京的“胶囊旅馆”大多少,却拥有一个液晶显示屏,一间自带的淋浴室,甚至还有一台小型的咖啡机。床铺上缠绕着好几条安全带似的皮带,看上去非常奇怪。
钉子上挂着一件连身衣,上面袖着姓名牌——“奥拉姆”,以及臂章,就像宇航服一样。臂章上有一个象征黑洞的漏斗状图案,图下还附有一行文字:“宇宙时间深海潜水艇一号”。真够蹩脚的,我想。不过,我倒是很想知道什么样的“深海潜水艇”会埋在莫哈韦沙漠下面。
我迅速冲了个澡,洗掉跨越大西洋飞行中沾染上的满身污垢,重新振作起来。连身衣十分合体。我将从伦敦带来的衣服锁在了衣柜里。
埃尔斯泰德在外面等着我。“衣服怎么样?它是智能织物制成的,具有自我清洁和温度调节功能。”
连身衣凉凉的,紧贴着皮肤,随着我的运动伸展收缩,没有半点阻滞。“我想要一件。”
他笑道:“这件送给你了。”
我们穿过甲板上的另一个舱口盖,下到更低的一层,进入一个更大的舱室。这里被埃尔斯泰德称为“舰桥”,大体上呈圆柱状。甲板、舱壁,甚至天花板的表面上都装有液晶显示屏,屏幕上正滚动着复杂的图形和数字。三把座椅悬浮于舱室的正中央,样式与客机上的豪华沙发椅相似。走过一条涂成白色的金属窄道,你便能来到座椅旁。座椅里装配有固定在托架上的液晶显示屏,你可以将其拉伸出来,放置在面前,以便于观察。
中间的座椅上坐着一个人,他四十岁上下,身材瘦小,神情专注。看上去他正忙得不可开交,一会儿看看舱壁上的显示数据,一会儿又瞅瞅面前的液晶屏。发现我们后,他打算站起来打招呼,但埃尔斯泰德立即做了个手势。“德国式的礼节就免了吧。我们三个人将会在未来几天里一道工作,所以没有必要去讲究什么繁文缛节。”
那个男人跟我握了握手。“我叫沃尔特·荣格。”他将“沃尔特”念成了“瓦尔塔”,从这种口音判断,我怀疑他应该是波斯裔德国人。
埃尔斯泰德拍着他的肩说:“沃尔特是我的魔鬼天才。这里的一切,包括‘深海潜水艇’和所有的仪器,都是他设计的。”
荣格点点头。“但这都是源自你的理想,埃尔斯泰德。”
埃尔斯泰德笑道:“还有我的钱。美国钞票和德国头脑携手创造历史,这不是第一次了,对吧,苏茜?现在船员已经到齐了。坐下吧,苏茜——你的位置是右边那个。系上安全带。”
我摆弄安全带时,荣格开始继续工作,而舱室里响起了低沉的嗡嗡声。我感觉到大量能量正在积聚。这一过程颇似宇航飞船升空前的情景。我甚至觉得,我们身处的这个装置会像导弹井中的“民兵”导弹一样,从地底呼啸而出。
为了迎接这一刻的来临,先期的准备工作可能已经进行了好几个小时,但我仍然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再次不寒而栗。
埃尔斯泰的朝我露齿一笑。“苏茜,你身上有没有什么挂件,比如小金盒什么的?”
我戴着一条十字架金项链,它是我五岁时妈妈送给我的。从那之后我就一直戴着。
“你能把它取下来,挂在面前的显示屏托架上么?”
我耸耸肩,照他的话做了。那条项链摇来晃去,反射着屏幕上的光。“我现在对我们要做什么还是一头雾水啊。”
“五分钟后你就会明白了。”
“实际上只有三分钟多一点了,”荣格说,“你们关上舰桥的门之后,五分钟倒计时就开始了。”
“那么只需要再等三分钟。我先前曾经给过你提示,苏茜——”
“宇宙勘探。这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我回忆起曾在“发现”频道见过的凝视着宇宙深处的大型轨道望远镜。宇宙学是一门观察的学问,它的研究对象是浩渺的太空,它的理论涉及到夐古的过去和杳远的未来。你如何才能够“勘探”它呢?
不过,我也找到了一些其他的线索。“我们在莫哈韦沙漠之中,毗邻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对吧?如果你想要与世隔绝的话,这里是个好地方。不过,这里同样能够方便地获得来自洛杉矶的科学家的帮助,空军基地还能够协助装卸重型物资……”我想起了那些绵延几公里的积木似的建筑,“你是不是在这里建了一台粒子加速器,埃尔斯泰德先生?”
“叫我埃尔斯泰德就可以了。你猜得不错,苏茜。但粒子加速器只是达到最终目的的工具而已。”
“但我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在沙漠下面埋一台‘深海潜水艇’。”
“还有一分钟。”荣格说。
我耸了耸肩。“容我直言,你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而我来这里的唯一价值是充当一名公正的见证者,我的工作就是在你的伟人传记中写下记录这一‘壮举’的一章。对吧?”
埃尔斯泰德笑了起来,显然并没有因为我的话而气恼。“你说得再准确不过了。可除了钱之外,你来这里还有别的原因么?”
“如果你成功了,那我无话可说。但如果你失败了,这一愚蠢举动将值得我大书特书。”
“很公平。我希望我们双方都能够如愿以偿。”
“还剩十五秒。”荣格说,“一切正常。十、九……”
“我想我们不需要倒计时。”埃尔斯泰德说。
于是我们静静地等待着。埃尔斯泰德看上去气定神闲,我的胸部猛地被安全带牢牢勒住。我心头一惊,连忙问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是在某种电梯里么?”
“看看你的项链,”埃尔斯泰德说,“我从‘联盟号’的宇航员那里学会的这个小把戏。”
十字架正飘浮在空中,挂链则蜿蜒盘绕。
“我们在做自由落体运动。”埃尔斯泰德说。
“为什么?怎么会这样?我们被埋在沙漠里啊。”
“现在不是了。”荣格说,“埃尔斯泰德,外部监视器已经启动。”
“它们是‘潜水艇’船壳上的摄像机。”埃尔斯泰德对我解释道,“沃尔特,让我们看看外面的情况。”
荣格敲击了一个控制键。舱壁上的数据立刻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此刻“深海潜水艇”外的景色。
群星璀璨。
“我们已经坠出地球了。”埃尔斯泰德说。星光下,他的笑容带着几分邪意。“而且,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坠入了时间之渊……”
我尖叫起来,然后狂吐不止。
埃尔斯泰德和荣格都已经做过准备训练。埃尔斯泰德有“联盟号”上的经历,他还送可怜的荣格去体验了几回喷射彗星上的失重感觉。而我呢,虽然止晕药止住了呕吐,但旅行开始的头几个小时里,我还是深感不适。我现在总算承认,自己的确踏上了所谓的“勘探”之旅——尽管对将要去的地方和如何前去的方式,我仍然没有半点头绪。
我将大部分时间花在舰桥之外的地方,大体摸清了这艘“深海潜水艇”的构造。当然,这是某种“移情”,即把注意力集中在各种装置和设备上,而不去想外面的状况。但我必须学会如何在失重状态下行动自如。
“深海潜水艇”的核心部分是一个高十米、宽五米的圆柱体,被三层甲板隔开。中间一层是舰桥,以我们三人的椅子为中心;上一层是生活区,包括卧舱、厨房和厕所,埃尔斯泰德最先领我经过的便是这一区域;下一层被密封了起来,里面有电脑库、封闭的生命维持系统,以及我们的能量源—— 一组小型的核电装置。你可以轻松地在失重的状态下穿梭于三层甲板之间,因为埃尔斯泰德借用了一些空间站的内部设计:舱壁上有维可牢粘合垫,以便你将钢笔和掌上电脑粘上去;色彩搭配对比鲜明,以便你形成准确的方向感。
中央圆柱体之外是由强化金属构成的球状船壳。船壳与圆柱体之间充斥着某种——呃,奇怪的物质。
那天晚上,我努力试着去安然入睡(我现在总算明白床铺上的皮带是干什么用的了)。但总是被噩梦惊醒。梦中我无依无靠,正不断地往下掉——我们也的确在往下掉。我甚至觉得,我们正在沿着一条笔直的通道坠入地心。
但后来荣格给我看了摄像机拍摄下的其他景象。摄像机镜头一转,我便看见了船壳本身,它有着圆滑的曲面,其上喷绘有一面星条旗和多幅埃尔斯泰德公司的标志,还沾着少许莫哈韦沙粒。镜头一旦从船壳转开,就会又充满群星的光辉。
“发射”后二十分钟,埃尔斯泰德通过内部通信器召唤我:“我们就要到达本次旅行的第一站了。你肯定想观看这一奇观。”
我不情愿地返回了舰桥,心里忐忑不安。三把座椅正悬浮在一片星海之中。我经过窄道,将自己固定在椅子上,这样做能使我感到比较安全——尽管现在船身并没有发生震动。
群星四合,星座的图形梦幻般变化着。在闪耀的星星背后,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一层薄纱,它拥有五彩缤纷的颜色,如同透过彩虹看见的一片云。我完全搞不清楚自己看到的是什么。
荣格正心无旁骛地操纵着机器。埃尔斯泰德则期待着我对这一奇观叹为观止,他向我解释道:“你看见的一切都经过了特殊处理,因为射到船壳上的光发生了蓝移,也就是多普勒位移。我们必须将强烈的光子流转化成适合肉眼观察的东西。”
通过交警使用的速度检测雷达技术,我知道多普勒位移与相对速度有关。“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蓝移?我们的速度怎么会这么快?”
“蓝移是由于我们坠入时间之渊造成的。”埃尔斯泰德说,“我们的速度正在不断提升,或许你可以从周围的不断涌现的星辰中看出端倪来。太阳只是围绕银河系中心的黑洞运行的一大群星星中的一个而已。在银河系之外,你可以看见仙女座星系。它与我们相距两百万光年,是人类裸眼可见的最远的深空天体。在我们来的那个时代,它仅仅是星空中的一块光斑。”
我现在看见的那片闪光的星云已经不再是斑点那么简单了。
荣格给我指出了星空中最亮的那颗星。“那是我们的太阳。我们还没有走得太远。”听到这句话,我感到有些放心,但我发现太阳似乎泛着淡淡的红色。
埃尔斯泰德大声道:“我想你该提问了,苏茜。最基本的两个问题应该是:我们是怎样穿越时间的,以及为什么要这么做。”
“或者,我应该问你是如何搞出如此惊人的骗局的。”
埃尔斯泰德又大笑起来,似乎不论我怎样冷嘲热讽,他都不会介意。“那你要先问哪个问题呢?”
“好吧。我们是怎样穿越时间的?”
埃尔斯泰德朝荣格点点头。“这应该由我们的工程师来回答。”
荣格说:“具体的技术解释起来十分复杂。但总的原理却很简单,那就是利用浮力……”
于是,我们的话题深入到粒子物理学领域。
宇宙是由几种成分构成的。你我这样的可见物质——重子组成的“正常”物质——只占宇宙的极小部分。此外更多的是“暗物质”,它是一种神秘的粒子,其存在只能通过与可见物质的引力作用来间接证明。它是如此难以捉摸,以至于到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发明高灵敏度探测仪之后,人类才第一次捕捉到了这种粒子。不过,上述两种物质加在一起也没有宇宙中的另一种成分多,那就是“暗能量”。
“‘暗能量’是一种反引力场,”埃尔斯泰德说,“它是宇宙加速膨胀的原因。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对一系列超新星进行观测之后,人们发现,大约在六十亿年前,宇宙开始加速膨胀,而宇宙的膨胀速度在‘大爆炸’之后就是在不断下降的。于是,我们了解到‘暗能量’正在逐渐发挥主导作用。”
荣格说:“在宇宙中任何一个时间的任何一处空间——比如这艘船,或者苏茜你自己的身体——都包含了这三种成分:‘暗物质’、‘轻物质’和‘暗能量’。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暗能量’的比例在不断增加。而我们正利用莫哈韦沙漠下的设备——”
“粒子加速器。”
“——寻找一种在特定空间中增强‘暗能量’的方法,具体地说,这个特定空间指的就是这艘‘深海潜水艇’内部。”
“但这究竟是怎样做到的呢?”我不解地问,“难道我们对‘暗能量’不是知之甚少么?”
埃尔斯泰德说:“你不需要把某种东西搞得一清二楚之后才去利用它。我的公司生产的手机利用了量子论原理,而人类花了一百年的时间才彻底弄清这一理论。至于具体的细节,抱歉,苏茜,那是商业机密,我不能告诉你。”
“那么,往这艘船里注入‘暗能量’之后会怎样呢?”
“会产生浮力,”荣格说,“苏茜,‘深海潜水艇’内部空间的构成成分已经与未来的物质基本无异,这里的‘未来’是指宇宙的绝大部分都充斥着‘暗能量’的时候。所以,这艘船能够无拘无束地在宇宙时间中穿行。它就如同是水舱里注满水的潜水艇,可以潜入宇宙时间的最深处,也就是异常渺远的未来。”
“可是,”我半信半疑地说,“水舱也有可能会被撑破呀。”
“哦,是的。”埃尔斯泰德说着指了指大大的方形红色逃生键。他和荣格的控制台上各有一个,而我的没有。“只要一按这个键,‘潜水艇’就会立即上浮。我可不愿死在宇宙时间的旋涡里。”
“我猜你肯定已经做过实验了吧?”
“用遥控探测器做过,”荣格说,“这次是‘潜水艇’的处女航。”
“你可以把它当成试飞。”埃尔斯泰德说,“很刺激,对吧?”
荣格凝视着墙上的显示屏。“星系并合开始了。”
埃尔斯泰德查看了一下他面前的显示器。“好戏上演了。苏茜,可能你也知道,我们的银河系与仙女座星系是本星系群中的两个庞然大物,而它们自诞生之日起便在相互靠拢。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它们终究会相撞。但我们就在未来,不是么?所以,敬请观赏吧……”
横贯天空的碟状星云被一片闪亮的光芒拦腰截断。我看见火花四溅:巨大的星体诞生、燃烧、死亡。每一次心跳都意味着数百万年的时光飞逝而过。
“我们在一个碟状星系的内部,”埃尔斯泰德嘟哝道,“这个星系插入了另一个碟状星系里。两者撞击时释放出的气体在受压后形成新的星体——对两个星系来说,这都是有史以来最壮观的造星运动。不过,对于两个星系中的生命而言,这却是灭顶之灾。”
我们周围的星星蜂拥而聚,持续进行着剧变。只有太阳仍岿然不动地燃烧着,发出红色的光芒——或许我们正在环绕它运行。仙女座星系的旋涡状结构开始解体。在我眼中,这一过程就像是喷泉在向外喷射五颜六色的泉水,只不过这里的“泉水”是群星、星云和星光长带组成。不过,那些光带只是昙花一现而已。
“表演已经结束了,”埃尔斯泰德说,“就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撞击生成了一个复杂的混合体。但它迅速冷却,演变为一个庞大的、扁平的椭圆状复合星系。这时,原先两个星系的旋涡状结构已经崩溃,造星运动中使用的气体也消耗殆尽。这真是一场奢侈的焰火表演啊。”
这一切可能只是电脑模拟出来的。我过去见过比这更加精致的虚拟现实图像,可是……“埃尔斯泰德,这次并合将会在什么时候发生?”
“你是说大致的时间?”
“对。”
“从我们来的时间算起,三十亿年后。”
我在苍穹中搜寻着太阳。它的颜色变得更加鲜艳,体形也更大了。“我们的太阳怎么了?”
“沃尔特,太阳步入红巨星阶段是在六十亿年之后吧?”
荣格检查了一下数据,耸肩道:“天体物理学家只可能进行预测。刚才的星系并合有可能扰乱了太阳的物理机制。”
埃尔斯泰德哼了一声:“屁话。你一定要将这些数据记录下来,荣格。我要拿回去糗一糗康奈尔大学的麦克纳利,让那个老学究乖乖认错……”
太阳忽然膨胀起来,形成一道占据半个天空的深红色的墙,表面上巨大的太阳黑子清晰可见。接着它开始向外抛射残余物质。有那么一小会儿,我们周围的空间中环绕着绿色、红色和蓝色的闪亮气体,如同北极光一般。但这片星云转瞬间便消散无踪了。
“这就是太阳的命运。”埃尔斯泰德说。
我问:“地球会怎么样?”
“即便没有被太阳吞噬,它现在也已经变成了一块表面覆盖着一层氮冰的矿渣。对此你怎么看呢,苏茜?伦敦、纽约、伯利恒和麦加,这些辉煌的城市都将灰飞烟灭。可惜我们摄像机的分辨率不够,难以观测到地球。”
“三十亿年。”我说,“人类还能存在多久?一百亿年?一千亿年?”
“哦,比那要长久得多。”埃尔斯泰德笑道。我开始讨厌他这样故弄玄虚了。
我发现我的金十字架仍在空中飘浮着。我一把抓住它,往脖子上一绕,然后系上挂扣。“我想回卧舱——”
荣格抓住我的胳膊。“不,等等。”
船开始摇晃起来。群星背后闪现出一道冷光。
“引力波。”荣格喃喃道,“这是位于两个星系中心的巨大黑洞并合造成的。随后还有余波,请稳住身子,不要乱动。”
“深海潜水艇”再次剧烈晃动起来,金属外壳嘎吱作响。我们坠入更深的时空之中。
第三天的中午,我正待在舰桥上,这时我们到达了本次旅行的第二站。
埃尔斯泰德端来了热腾腾的午餐,它们刚从微波炉里拿出来,装在陶瓷盘子里。我们在各自的座位上用餐,盘子固定在托架上。我要了一份意大利烤面。同我预想的一样,船上的厨房只提供“宇航员食品”:压缩饼干,以及被胶水似的酱汁粘在盘子上的热食。我听说俄国人在饮食方面比美国佬做得更好。
我们的四周,新形成的椭圆星系中的群星正在默默涌现。随着亿万年光阴的流逝,它们的光辉也渐渐褪去。
“深度二百五十亿年。”荣格说,“是‘大坍缩’的理论预期时间。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紧张起来,停止了进食。“‘大坍缩’,那是与‘大爆炸’相反的玩意儿,对吧?”
“是的。”埃尔斯泰德说。
“在‘大坍缩’中,所有的物质,甚至连时间和空间都会消失,对吧?”
“是的。”
“包括我们?”
“有这种可能——”
荣格做了个噤声的手势。
我屏住呼吸,紧抓住座椅上的扶手,但这只是徒劳。
什么都没有发生。星星继续闪耀,然后静静黯淡下去。
“我们通过了这一站,”荣格说,“下一站是‘大撕裂’,在一百五十亿年之后。”他瞥了一眼计时器,“或许还要等一个小时。”说完,他又开始吃起饭来。
“这么说,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大坍缩’啰?”
“不存在‘大坍缩’。”埃尔斯泰德说,“请你把这记下来,记者小姐。我们已经取得了第一个宇宙大发现。苏茜,我觉得你应该问我第二个基本问题了。”
我点头道:“那么,你为什么要搞这次宇宙勘探呢?”
“原因很简单,为了找到一个最根本问题的答案:我们人类最终的结局是什么?”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起来,“苏茜,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宇宙看起来十分简单。宇宙中的主导力量就是引力——所有的人对此都深信不疑。我们认为宇宙是在一次‘大爆炸’中产生的,而引力决定了宇宙的未来。如果宇宙的物质密度过高,引力过强,那么它就会在达到一个半径极值后开始坍缩。否则,宇宙就将永远地膨胀下去。也就是说,宇宙的结局要么是‘大坍缩’,要么是永无止境的扩散。可是,这一简单的图景却被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系列对遥远超新星的观测结果打得粉碎。现在,这个终极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暗能量’的性质,而人类对于‘暗能量’还几乎一无所知。
“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即假设‘暗能量’的密度逐渐降低,甚至变为负值,那么‘暗能量’就会表现为引力,宇宙膨胀的速度将会越来越慢,最终发生逆转,导致‘大坍缩’。但我们已经经历了最有可能发生‘暗能量’坍缩的那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证明了‘暗能量’的一些属性,你明白吗?这次勘探所研究的不仅仅是宇宙,还包括基础物理。”
我焦急地瞟了眼荣格,他正入神地监视着计时器上的读数。“那么‘大撕裂’会不会发生呢?”
“‘大撕裂’假说是建立在另一套‘暗能量’理论模型之上的,其设想的场面也更加激动人心。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宇宙空间的扩展,‘暗能量’产生的排斥力将越来越强,足以撕开所有坚固的星系,最后甚至连原子核也可能被撕开。这一结果将会突如其来,并且是毁灭性的。”
“离‘大撕裂’还有五分钟。”荣格说。
我再次紧抓住我的座椅扶手。
“现在你知道我的理想了吧?”埃尔斯泰德说,“我要通过直接观察宇宙的未来,去探究我们注定要遭受的是何种命运,顺便证实众多基础物理模型谁对谁错。这是多么伟大的理想啊!你知道,我只做了很少的事情,便赚了很多的钱。我的公司生产的内置式手机并没有多大的改进,却打败了同行业的所有对手,给我带来了数以十亿计的财富,但这一看似辉煌的成就将在一个世纪后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与之相反的是,这次宇宙勘探所取得的成果将会永远激发人类的想象。我知道大家会说我好大喜功,但我已经生了孩子,并给了他们难以置信的财产。我还能把钱花到什么地方去?……”
就在埃尔斯泰德喋喋不休地自我吹捧的同时,五分钟过去了。然后是六分钟,七分钟——我们依旧安然无恙。没有发生“大撕裂”,又一个“暗能量”模型宣告失败。
我回到卧舱,将吃下去的东西全都吐了出来。
第四天的航行相对沉闷。我们三人坐在舰桥上,一边嚼着半生不熟的电视便餐,一边观看着宇宙中上演的大戏。
我们正在潜入更加辽远的未来。在我们面临的这个“暗能量”模型中,“暗能量”的密度似乎始终保持着恒定不变,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按照埃尔斯泰德的说法,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尽管我们的潜入速度越来越快,但在宇宙发展到另一个关键点之前,它还必须经历一段漫长的过程。
于是,我们看见的一千亿年之后的宇宙变成了这副模样:宇宙膨胀将其他星系“带出了我们的宇宙视界”(荣格语),它们的光再也无法抵达我们;而我们的椭圆星系被孤零零地抛在了后面,仿佛是空荡荡的教堂中的一盏昏惨惨的蜡烛。
椭圆星系越来越衰弱。先前星系并合过程中的造星运动消耗了大量的物质,但最后却只留下了大量小星体,不断补充着它们那少得可怜的氢储备。但即便是这些星体也摆脱不了死亡的命运。
我开始思索起生命来。“在我们周围,无数与我们类似的文明可能正无声无息地兴起、衰亡,而我们却无法感知到它们的存在。”的确如此,我们前进得太快了。
埃尔斯泰德接住话头说:“如果此时外面真有生命的话,你认为是否包括我们人类?就算人类从星系并合中幸存下来,我们后代的模样还会与我们相同么?”他扫了眼飘浮在我喉咙前的十字架,“你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么,苏茜?”
“算是吧。”我诞生在一个奉行天主教的家庭中,我同父母一道做弥撒,我认可教会的凝聚力,而且我对其他教派和不信教者表现出足够的宽容,“你呢?”
他轻蔑地说:“我不是,但我的父母信教,你或许可以凭我的名字猜出来。想想看吧,在我们来的那个时代,基督教的历史只有几千年。有些神祇存在的时间更长些,但大多数都被遗忘了,比如,我们不知道巨石阵要拜祭的是何方神灵。人类文明不大可能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崇拜同一个神。
“但是,假设人类能够延续一百万年,或者一千万年——大多数种类的哺乳动物都无法延续如此长的时间——人类将会被时光雕琢成什么样子?难道对于某个神的记忆可以一直保持这么久么?可是,如果你笃信基督、阿拉,或者另外的‘唯一真神’的话,你就必须要相信神是永恒不灭的。”
我沉思片刻后说:“这两种情况——基督教信仰的最终抛弃,或者基督教信仰的永远坚持——我现在很难说它们中哪个更有可能发生。”
“的确如此。不过,请你思考得更深入一点。人类灭绝之后,世界将会怎样?最后一个人类将会给半人马座阿尔法星的八脚怪物施洗礼么?对基督的敬仰会在异族的头脑中延续么?倘若宇宙中所有的智慧生命都灭亡了怎么办?在没有思想、甚至没有生命的宇宙中,基督教还有必要存在么?你必须相信基督教永存,否则信仰还有什么意义呢?”
埃尔斯泰德就这样肆无忌惮地挑战着我的信仰,荣格向我投来同情的目光,但我不以为意,因为我那所剩不多的信仰并不足以使我对此怒不可遏。
我觉得埃尔斯泰德之所以总喜欢找我的茬儿,是因为他百无聊赖——他无法忍受宇宙终结前的漫长等待。
第五天,群星开始熄灭。
在很短的时间内,天空中布满了它们的遗骸:黑洞、中子星、巨星的残余物,而我们的太阳变成了白矮星,慢慢消隐进深邃的太空中。偶尔会有一抹亮光闪现,那是某颗倒霉的死星落入了黑洞,或者两颗矮星相撞后燃烧了起来。荣格说,我们的太阳最终会坍缩成一个碳元素构成的巨大水晶球,那时它的温度会大大降低,你甚至可以用手去触摸它。这样的场景非常神奇,但我们却没有办法看到。
第六天,银河系崩毁。一次次的随机相遇将星星一颗接一颗地抛出银河系的引力井。这一不停歇的蒸发过程使星空变得更加黑暗。荣格告诉我,银河系在经过万亿亿年后,终于彻底消散了。
万亿亿年——我努力思考这究竟是个怎样的概念:它比之于从“大爆炸”到人类诞生的时间,就如同我们来时宇宙的年龄比之于一年。然而,这样的对比给我带来的震撼稍纵即逝,因为我们正在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坠入更加深不可测的时间之中。
宇宙继续膨胀,它那单调的物理变化仍在进行。除了我们的呼吸声和气体洗涤器转动时的呜呜声外,“深海潜水艇”里没有半点声响。
第七天,最后的残星魅影——红外线的踪迹——也都一一隐去了。成功地将星系分离之后,宇宙膨胀把魔爪伸进了单个星体之间。最后,太阳的残余物被隔离在自己的宇宙视界里:在太阳的宇宙之中,只有太阳自己而已。
随着第七天的过去,即使是钻石一般的太阳也开始分崩离析。
荣格在“深海潜水艇”的外壳上安装了一组粒子探测器。他将探测器收集到的信号通过扬声器播放出来,我们便听见了漆黑的宇宙传来的轻柔的噼啪声。
“质子。”埃尔斯泰德说,“这是质子分裂成夸克时发出的声音——从极其长远的角度看,就算重子是也不稳定的。另一个理论又得到了证明!它们应该给我诺贝尔奖。”
“那么还将发生什么呢?”
“这都取决于明天的发现,苏茜。”
那天晚上,没有一个人回去睡觉。我们拿出卧舱里的毛毯,并排坐在自己的座椅里,宇宙中仅存的一点光照在我们的脸上。无人入睡,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但也没有人提议关掉显示屏,将那个似乎永无尽头的恐怖夜晚排斥在外。我呆呆地看着表,我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
终于,第八天来临了。
那个时候,我们完全无法理解我们经历的事情。但到了后来,我们却用尽全力试图重新将其组织起来。
我们聚在一起,因为我们认为自己在宇宙中是孤独的。但我们错了,人类从来都不孤独。
生命和意识在一百个不同的中心诞生,然后向外扩展到整个银河系。泱泱帝国开疆辟土,纷纷战事无休无止,煌煌文明沉浮兴衰,从战火中锤炼出比以前更加顽强的生命。
尽管早先出现的人类并没有能够幸存下来,加入这次银河系文明大碰撞,但地球的废墟被后来者发现了,人类的历史也被后来者了解到。
接着,银河系与仙女座星系发生并合。两艘承载着自身历史与文明、由无数星体构成的超级战舰之间惊天动地的撞击,给两个星系文明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而随后而来的黑暗岁月中的战争更给这一创口雪上加霜。
可是,这场撞击带来了新的融合。群星中诞生了新的意识,它们如同是即将倾倒的树木中的鸟儿,聚集成一个更加强大、智慧的文明。不过,这个文明比先前的任何一个都更温和。
在随后的漫长岁月中,文明不再崇尚征服,而是注重团结,不再追求获取,而是强调保存。无数的大型图书馆被修建起来,知识也得到了坚定的捍卫。
然而,宇宙却仍在衰退。
随着银河系的蒸发,统一的文明逐渐分裂成众多的邦国。更糟糕的是,群星离彼此越来越远,宇宙的复杂度开始降低,古老的层级体系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信息丢失了,所有的历史也都湮没无闻。
残存的文明将资源积聚在一块儿,然后是生命个体本身。这样,在太阳的宇宙视界之内,最后只剩下一个单独的意识,储存着残缺不全的记忆。
宇宙仍在冷凝。埃尔斯泰德的最后一个宇宙发现是,我们无法从无穷无尽的膨胀中获得任何宽慰。质子解体后,所有的物质都变成了一团光子、电子、正电子和中微子组成的粒子云,而宇宙膨胀会继续将这些残余物也拉开。最终,每一个粒子都将成为自己宇宙视界中的唯一存在。而到那个时候,宇宙的复杂度将降为零,意识也会停止。
试想一下!你躺在那里,作为太阳系唯一的意识,困于宇宙时间之中,如同被浸入正在逐渐凝固的冰水中一样。你模模糊糊地记得你以前的身份,以及你掬起的一捧星光。而现在你却无法动弹。宇宙的持续膨胀将你的记忆一点点撕碎,等待你的是彻底的遗忘。最后,你只剩下愤怒与痛苦,以及对先你而逝者的嫉妒。
而到这时,你或许才会感到一丝宽慰。
在地球的海洋中,生命大量集中在洋面附近。在阳光的照耀下,这里生活着一层厚厚的浮游生物,它们是维系生物链的微型森林。但在鱼类竞食的过程中,食物的渣滓碎屑将会落入下层黢黑的深海,那里游弋着长有大眼、巨嘴和尖牙的怪鱼,它们生活在贫瘠的生态系统中,只能靠从阳光充足的上层落下的、其他生物的残羹剩饭为生。
你现在便处于时间的深海里。在上层光明的、能量充足的过去,时间机器被一次次发明出来,谨慎的时间旅行者利用它们潜入下层幽远的未来……
你被囚禁在寒冷与黑暗之中。但偶尔也会有一块来自灿烂往昔的残渣穿越重重时光落向你,带来一点物质与能量,以及最重要的复杂度。于是你获得了短暂的复活——或者说,至少能够再次享受思考的奢侈。
这艘“深海潜水艇”—— 一台行为不够谨慎的时间机器——就像是即将饿毙者口中的一只新鲜草莓。你咬下去,味道却是苦涩的……
“深海潜水艇”翻滚振颤。舱壁上的红色警报信号一个劲儿地乱闪。荣格和埃尔斯泰德互相咆哮。这次遇到的情况比先前星系并和造成的引力波糟糕得多。
但我担心的并不是“潜水艇”,而是我自己的大脑。
我能感到另一个意识存在于我的大脑里,仿佛一只搅动我颅腔的大手。它啃食着我的记忆、我的人格、我的生命——它要吞噬掉我所有的一切。与此同时,我也能感觉到它是一种完全超越我的智慧,它博大空寂的思想如同是一座荒废的博物馆。我还感觉到了嫉妒、怜悯与悔恨。我禁不住潸然泪下,为我自己,也为我脑中的另一个意识。
后来,这个意识消退了。但我的头颅似乎仍敞开着,将冰冷的大脑暴露在空气之中。
我看见荣格发疯似的猛摁他面前的逃生键。然后我晕了过去。
我们裹着毯子坐在莫哈韦沙漠的烈日之下。将我们从破损不堪的“深海潜水艇”中拉出来之后,医护人员本来打算送我们去医院,但我们却不愿意离开阳光和温暖。尽管医生和技师在周围忙来忙去,可我们却觉得整个宇宙中似乎只存在我们三个孤独的个体。
其实,我们并不孤独。
从“下面”返回现在的八天旅程里,我们一直在努力将经历的事件重组起来,将我们七零八碎的印象拼凑成一个整体。到地面之后,我们仍在争论不休。
“那头时间之鲨,”埃尔斯泰德说,“本来可以毁了我们,但它却没有。为什么呢?”
“因为它可怜我们,”我说,“就这么简单。它的确会吞噬掉时间机器,但我们的机器却像热气球一样原始,甚至是第一台前进到那么远的机器。时间之鲨在我们身上看到了某种它失去的东西:潜力,或者说希望。它无法毁灭我们,正如痛苦的老人不忍心杀死刚出生的婴儿。”
“这个观点很有趣,”埃尔斯泰德说,“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可时间之鲨就是我们呀。”荣格说,“它是两个并和星系中所有意识的结合体,或者是其中的一块碎片。”
“它不是我们,”我无力地说,“你难道没感觉到么?它身上没有半点人类的影子。”
回来的路上,我们始终都在争论这个问题。而埃尔斯泰德怂恿我们争论的唯一理由是,他不肯相信人类终将灭绝。“有可能是这样,但也有可能不是这样。”他同我们一样困惑,但他裹在毯子下面,揉搓着双手说:“我们必须保证这种事情不会发生。”
荣格和我瞪着他。我问:“你在说什么呀?”
“我们带回了海量的数据。或许我们能借此找出人类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然后避免人类走向灭绝。”
我说:“可即使你做成了这件事,那又如何摆脱得了最终的命运呢?当宇宙膨胀将最后的粒子拉开的时候,复杂度将会降为零——”
“难道只有这一种可能的结局么?”埃尔斯泰德反问道,然后开始谈论其他的物理理论:“暗能量”场的强度可能会降低,并延缓宇宙膨胀的速度;或者,一种叫做“第五元素”的更神奇的力量将在最后的基本粒子仍能保持相互联系前阻止膨胀继续,而生命和意识便能够延续下去——尽管其速度会变得缓慢无比。“但故事不会结束,”他说,“不会结束。”
“埃尔斯泰德,”在我们共同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我尽量使自己语气平和,“宇宙不是你想要的那个样子。宇宙与你愿意接受的理论模型不相符。我们亲眼见证过的。”
他一点都不沮丧。“那么,我们就必须找到一个修正的方法,让宇宙去符合那个理论,或者前去另一个我们更加喜欢的宇宙。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研究计划的细节。我一直都相信,不论未来怎样——‘大坍缩’也好,‘大撕裂’也罢,或者只是无穷无尽的膨胀——我们都能有办法使信息在终极毁灭中保留下来——生命肯定能逃脱灭绝的命运。我所有的行动都是建立在这一信仰之上的。”他紧盯着我,憔悴的脸上,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你愿意与我一起奋斗么?”
上面所有的事情都是两年前发生的。
我没有回英国。我再也无法忍受黑暗和阴冷,甚至海洋。我购买了科罗拉多州的一座山顶房屋,那里能最大限度地沐浴阳光,并且远离海洋。我家离山顶很近,每天早晨我都会到那里散步。
我按照约定写了相关的报道。我挣到了我该得的欧元。
我结了婚。我和丈夫正打算生个孩子。我觉得,通过繁衍后代,我或许可以稍稍减慢宇宙死亡的步伐。我一直与沃尔特·荣格保持着联系。我希望他的孩子能与我的孩子成为好朋友。
我开始重新做弥撒。聆听古老的《圣经》选段时,我说不清自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不过,我明白埃尔斯泰德至少有一点是正确的:时间的无尽延续,以及所有一切的消亡,这对于任何一种信仰来说都是终极挑战。或许在几百万年后,人类将会拥有足够的智慧去解决这一矛盾,但现在,我宁愿去等待。
众所周知,圣约翰·埃尔斯泰德又建造了一艘勘探船——“宇宙时间深海潜水艇二号”——它比第一艘更大,功能也更强。埃尔斯泰德还招募到一批与他志同道合的人。我拒绝了他的邀请,但我将我的十字架项链送给了他。
埃尔斯泰德又一次潜入了时间之渊,去挑战他无法接受的宿命。但他还会回来的。
每日荐书

去年年前,我最后一次见小玲,是在我导......

莫名的,在一片沉默之中,我突然接收到......
最热文章

人工智能写科幻小说,和作家写科幻小说有什么不一样?

德国概念设计师Paul Siedler的场景创作,宏大气派。

《静音》是一部 Netflix 电影。尽管 Netflix 过去一年在原创电影上的表现并不如预期,但是《静音》仍让人颇为期待

最近,美国最大的经济研究机构——全国经济研究所(NBER,全美超过一半的诺奖经济学得主都曾是该机构的成员)发布了一份报告,全面分析了 1990 到 2007 年的劳动力市场情况。\n

J·J·艾布拉姆斯显然有很多科洛弗电影在他那神秘的盒子里。\n

我们都知道,到处都在重启;我们也知道,如果有钱,啥都能重启。所以,会不会被重启算不上是个问题,只能问什么时候会被重启。自然而然地,世界各地的各种重启现象衍生出了一个有趣的猜猜游戏:哪一部老作品会是下一个接受这种待遇的?\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