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任青 图/姚凯
1
还魂尸送来的时候,面部只有模糊的轮廓,但老太太依然认得出那是自己的儿子。
她和死者面对面坐着,一言不发,看着五官和毛发自动塑造成型。他的皮肤湿润极了,不像死人,而像个刚出生的婴儿,新生的纹理在皮肤表面漂浮、固定,如海流在北欧峡湾逐渐雕刻出悬崖峭壁。他的眼睛越来越深、鼻子逐渐高耸起来,左脸上慢慢浮现出一块伤疤,是小时候摔倒在轧花机上留下的。那块伤疤慢慢由粉转红、变成褐色,缩小面积,固定在皮肤的表层,形状如儿子离家前一模一样。
老太太深陷在藤椅中,被奇观吸引、被恐惧攫住,身体动弹不得,呼吸声仿佛细小的灰尘降落在角落里。
十分钟后,死亡通知书姗姗来迟,同纸张一起来的还有乡会计和邮递员。会计瞪了邮递员一眼,责备他速度奇慢,竟把通知书落在还魂尸后送达。老太太终于扶着藤椅站起来,手却抖成筛糠,认不出纸上的字。会计好心给她念道:
兹有工兵王氏信光,殁于春月廿八日。马革裹尸,美名咏诵,光沉紫电,忠烈可风。
老太太看着纸,喉咙里发出猫叫般不清不楚的呜咽声,又转头瞧瞧屋里的怪物。那具还魂尸紧闭双眼,全身伴随胸部起伏慢慢抖动。他的肤色越来越深、头发越来越密,血管变得更细,在肌肤之下逐渐遁于无形。会计控制自己不去盯着怪物,从随身夹子抽出一份表格,开始与老太太核算。
“抚恤金:计信用点二十六万。明日入账,次周凭亲缘证明、死亡通知可取。”
老太太似懂非懂地点点头。还魂尸突然爆发出一阵响亮的打嗝声。
“他有……有其他继承人吗?”
老太太摇摇头,嘴角耷拉下来,眼里终于涌出大颗大颗的泪珠。
“嗨,大娘!”邮递员开口安慰她,“别伤心了,你看,不止你一家,我这里还有一摞呢!”
说完,他把手伸进邮件袋,掏出厚厚的一摞邮件,都用统一的颜色印刷,侧面的颜料排成一条褐色的长龙。见得此景,老太太用手拍着大腿,高声痛哭起来。
“可他们都没有还魂尸!看吧,你是唯一拥有还魂尸的人,因为你的儿子炸成了碎片,只剩了一粒芯片,不幸中的幸……”
“别说啦!”会计大声打断他,“去送你的信吧!”
“可我还想……”
“有什么好奇的!”会计踹了他一脚。邮递员悻悻地走出门去,最后回头望了一眼,恐惧的表情出现在他脸上——
“那尸体,睁开眼睛啦!”
2
还魂尸彻底变成了儿子的样子,他现在睁开了眼睛,慢慢转动着眼珠。屋里的几个人屏住呼吸,全都一动不动。老太太停止哭泣,向前挪了一步。
“当心,大娘!”会计扯住她。
还魂尸忽地一下站了起来,可是没站稳,又坐了回去。看见怪物站起来,会计和邮递员尖叫着向后退。还魂尸转头看看他们,张开嘴,一言不发,棕色的眼睛仿佛直勾勾地瞪进虚空里。
“我走了。”邮递员说,“大娘,我可对您的遭遇深表同情。”
说完,他转身跑出房门。“懦夫!”会计说,他的双腿发软,动弹不得,只得勉强用脚掌慢慢向后蹭。没等缓过神来,邮递员又跑了回来。
“技术员来了!”他说。
“终于来了。”会计长出一口气。一个个子不高的年轻人跟随邮递员进来,他的头顶染了一撮掺杂褐色的黄发,手上拿着带箱的大喷枪,制服沾满斑斑白点,身上挂着一丝破破烂烂的蜘蛛网子。
“怎么是你?”会计问,“市里的技术员呢?”
“市里的专家?他出了事故,车子翻进沟里,腿摔断啦。”年轻人顿上一顿,“上边说,只能让我来讲讲了。”
“你讲,你懂吗?”
“他们给我传了资料。说实话,我懂的也不多,要是问我化肥啦、农药啦,还能……”
“这样就行,”会计打断他,“快讲讲这个鬼东西,它已经快把我们吓死啦!”
“好,知无不言!”年轻人自己拉个椅子,却没敢坐下,扶着把手站在一边,“这是一类生化人,刚刚开发,用于死人的意识转移,人们都叫它还魂尸。”
“很贴切的名字。”会计说,“但这怪物有啥用处?”
“能给人安慰吧,”技术员说,“说不定技术成熟了,大人物们会争先恐后地入住,长生不败、永垂不朽。”
“到那时候,原主和生化人打起来,怎么办?”
“这……就不是咱该关心的了。”
“它现在是活的吗?”邮递员指着四体僵硬的怪物问。
“是啊。它的肉体刚刚形成,可能意识仍在构建。”技术员说,然后转向老太太,“资料上写,王氏信光阵亡时,头部植入芯片也遭到损坏,他们能够恢复提取的数据有限,所以生化人的人格是不完整的。大娘,他们已尽了最大努力。”
老太太面露恐惧地点点头。
“上边说,还魂尸仍在测试阶段,优先供给阵亡将士家属使用,数量有限。因为您的儿子他……尸骨无存了,所以向您派发一个,希望能够带来短暂安慰。”
“短暂安慰?”会计插话道。
技术员耸耸肩,“两周后,他们会把个体收回去,提取运行资料,再进行研究完善。”
“研究完了,能还给她们吗?”
“不知道,这玩意儿据说挺贵的,不过……”技术员拍拍椅子背,仿佛那儿贴着一个帮腔说话的电钮,“和您的儿子享受多出来的两周吧,这种机会不是人人都有,别人想要的话,恐怕得上阎王爷那儿找寻了!”
“他是我的儿子吗?”老太太突然开口问。
“他是个生化人,”技术员说,“这么说吧,人们借助先进技术,把您儿子残存的意识和记忆,移植进生化人的脑子。他就相当于您的儿子,只是记忆不太完整,并且给人感觉……有点奇怪。”
“我不明白。先生,他和我的儿子长得一模一样,他是我儿子吗?”老太太坚持追问。
“大娘,从定义上讲,他是个……”
“天哪!”邮递员双手指天,打断了年轻人的讲解,“你讲这么多,她能懂吗?给她个明白话吧,我还有一摞通知书要发呢!”
“好吧,”技术员说,“是!他的确……算是你的儿子!”老太太抿起嘴巴,点点头,眼睛动了一下。角落里突然传来声音,大家齐刷刷看过去——那个刚刚出生的人竟自己挣扎着站了起来。他看着大伙儿,缓了一会儿,慢慢开口说:“我饿了。”
人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说话,也不敢动,耳朵里只听见唰唰唰的杂音,那是风把满枝树叶吹翻过来的声响。技术员从椅子上挪开手,觉得都是汗,风一吹凉凉的。
“你问他要吃什么?”会计说,他把手放在腰间,就像那儿真有把无形的佩枪。
“你想吃啥啊?”老太太问。
“蒜苗炒肉。”还魂尸说。
“是我儿子!”母亲大哭起来。
3
秘制蒜苗炒肉的做法——瘦肉、五花切薄片,肉片用酱油腌过,蒜苗用盐腌过,五花肉下锅煸出油,再放瘦肉下锅炒熟,最后放蒜苗段和辣椒丝,加盐、酱油炒好,起锅淋少许麻油即可。
还魂尸坐在桌边,连吃了三碗,雪白的背部一耸一耸。吃完饭,他抱着膝盖,蜷缩在椅子上,不言不语。
“信……光,你冷不冷?”
“冷。”他说。
老太急忙翻箱倒柜,找出儿子的衣服。怪人笨拙地把秋衣穿上,却怎么也穿不进裤子,老太太帮他把裤子提好,腰带扎上。
“信光,你瘦了。”她说。
还魂尸点点头,抬眼看看她,一言不发。
“唉,你遭罪了!”老太太攥住还魂尸的手,那手冰凉冰凉的,她赶紧把它们捂在怀里,“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怪物再次点点头,他耐心等老太太掉完泪,慢慢把手抽出来,盘腿在椅子上坐定,面朝北方闭上眼睛。
老太太在旁边待了一会儿,开口问:“仗……打得怎么样?”
“什么怎样?”
“就是战场有什么事儿啊……能打赢吗?主要是你怎么……怎么负的伤?”
“忘了,”儿子把眼睁开,“好多事都忘了,忘光了。”说完,他又把眼睛闭上,肚里发出与上午一模一样、打嗝般的巨响。嗝声好一阵才过去。老太太坐在旁边,待了一会儿,欲言又止。
“你先休息吧!”她说,然后轻轻退到外屋去。
晚上,王氏信光在家里睡了一觉,却没睡踏实,半夜惊醒了好几次。最后一次醒来后,他睡不着了,静静地躺在床上,看着墙上挂的旧钟表——6时15分。意识逐渐清晰,这是他第一次认识到时间概念,时间在一秒秒地流逝,真奇妙,昨天是他出生的日子,但他却感觉自己并不是个新人,出生前的时间也并非一片混沌。他看着秒针,滴答、滴答,一天有24个小时,一小时有3600秒,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把每一秒再分成若干个单位来体验,但他没有这样做。他现在是人类,他在学习王氏信光、学脑中本能、学所有的人类那样按分秒来感受时间。6时17分过去了,下一个阶段是6时18分,他想,窗外阳光很好,窗台有谷粒,应该会有鸟儿落下来。
思绪未及落定,一只鸟儿突然扑来,飞降在砖红色的窗台上。
老太太家有具还魂尸的消息很快在附近传开。下午,家里被围得水泄不通。邻居们争相前来询问亲人的事,孤老寡妇们像油炸的面糊,把王氏信光团团包裹。
“——我的儿子怎么死的,他说过什么话吗,有什么遗言吗?”
“我的丈夫怎么样了,你在部队见过他吗?”
“战场是什么样的,我们能胜利吗?”
面对这些问题,儿子总能做出不那么得体的回答:
“不知道。”
“不清楚。”
“对不起,真的忘记了。”
后来,老太太趴在厨房睡着了,天黑之后才醒来。她走到院子里,发现街坊已经散尽,留下一地垃圾,风越来越大,只剩一只狗在冲着还魂尸狂吠。老太太拿出棍子,把狗赶到门外。可它并不走远,在门边的竹竿堆旁趴了下来。她刚刚复生的儿子仍然坐在桌边,脊背保持笔挺的姿势。
“快睡吧,信光。”老太太说。
儿子指了指门边的黄狗。
“这动物,怎么说?”
“狗。”老太太说。
“狗。”他重复道,满意地点点头。
“去睡吧。”
“好,”儿子说,“等我恢复好了,学会帮你干活。”
“嗯……好,好孩子。”老太太说,“你在哪屋睡啊?跟我睡一屋吗?”
“再说吧。先回厨房。”
“怎么了?”
“锅倒了。”
话音未定,厨房里传来哐叽一声,那是巨大的蒸锅倾覆的声音,有个圆圆的铁篦子从门里滚出来,滚到草丛的边缘,立在那里,不动不摇。
4
收拾好物品,打扫好庭院,两个人才回到床上。这是复生后的第二个晚上,王氏信光做了个梦。在梦里,他见到一匹白色的骏马在厚厚的冰上行走,冰下是重重叠叠的残肢和深渊不灭的火焰。“马。”他记得这个词。梦里的冰太滑,那匹白马跑不起来,它失了前蹄,跪倒在坚硬的地面上。血涌出来,流淌到士兵们的鞋跟下。他低头看看自己的鞋,胶鞋掉了底,地面磨得脚生疼,头顶的燃烧弹把天空映得如同白昼,环绕四周的有万年前的斧石、千年前的车马、百年前的巨炮,两轮圆月在古战场上空熠熠生辉。王氏信光穿着掉了底的胶鞋走在战场上,封冻的河流让他慢慢失去意识,他忘记了自己是谁,只是跟随云雾般缭袅的指令,向末日缓慢地冲锋。在那个冰冻的晚上,月光下的一切都成为慢动作,对面军队的炮火成为意识的标枪,地雷存在于时空的每个角落,炸弹投射过来,碎片在空气中游泳,裹挟着夜幕与弹痕缓慢地消逝。
信光在消逝的秽雾中挣扎,在梦中拼凑着残缺的记忆,首先看到了本家叔叔,他比自己小一岁,却长一辈,是骄傲的飞行兵。王牌飞行手王氏信虎,在有大学可读的日子里,他便是飞行冠军,曾独自一人穿过峡谷、飞跃神山。战场上,他用身体撞烂三名敌兵,血肉如春雨般飘洒。他梦见了炊事兵安师傅,安师傅是缺少一条腿的残疾兵。工兵营人手不足时,炊事兵亲自披挂上阵,但他只会依赖设备,铁脚感受不到土地的触感。他不知道地雷和好土感觉是不同的,不知道触碰引线地雷会飞到你的脖颈里,他除了做饭,什么都不知道,但死亡知道他,死亡知晓一切。他还梦见了班长镜子男爵,班长因为迷信而得到这个名号。他总是把一面镜子挂在腰间,拴在皮带的扣眼上。他总在下午沏一杯糖水当作咖啡。在一块猩红色的盆地里,信光把他的身体从燃烧的机械中拖出来,他的腰上没有挂镜子,信光想,镜子一定落在了战车里。他梦见了女兵达娜·科拉帕洛娃,达娜长着一头亮褐色的秀发,她……
现在,这些人都不在了,他们被战争吞噬,化为废墟中的微尘,自虚空中来,归于虚空中去。
白马再次嘶鸣的时候,梦一下子醒了。信光猛地从床铺上坐起来,口中发出啸叫。老太太点亮了灯。他的瞳孔缩小,脑袋剧痛起来,“妈妈!”他尖厉地喊道。老太太已经数年没有听过这样的声音,她觉得这声音很美、很辽阔。
“别怕,已经早上了,”老太太说,“信光,信光。”
5
白天,信光学东西非常快。第一个周末的下午,他已经学会使用手扶农机耕作,只是有时面对松软的土地,他犹豫一下才敢走过去。傍晚时分,技术员回到村里,头顶沾满花粉,身上的蛛网似乎更多了。
“大娘,你和他相处得怎样?”
“我的儿子,他像个小孩。”老太太笑着说,“他一顿能吃好几碗面条。”
技术员也笑了起来。“我有些事情要告诉你,”他说,“不要让他的耳朵进水,普通的水还好,一定不能让酸性物质滴进去,若毁掉自适芯片,他就彻底变成傻子了。”
“当然,”老太太说,“耳朵进水,正常人都受不了,何况他在战场负过伤。”
技术员张张嘴,欲言又止,只好笑着和老太太告别,“祝你们健康!”技术员走后,母子二人就着微风,沿着土坡和田垄向外走,一直走到村子的尽头。那里的房屋越来越少,小小的坟头却越来越多。在一块堤坝和树林夹成的菱形土地,两个人停下脚步。
“这是咱家祖坟,你记得吗?”老太太问。信光摇摇头。
老太太叹口气,往南走了几步,指着一个立有灰色石碑的坟头说:“这是你爹的坟,记得吗?”
信光想了想,没有回答。老太太接着说:“我死了,得和他埋在一起,这事交给你办。”还魂尸点点头,把这件事牢牢存进脑袋里。他记住了坟地的位置、特征、爹的石碑、上面刻下的字迹。他看到坟头附近有棵大型植物,没有叶子,光秃秃的,根却繁茂,把地都拱了起来。
“怎么有棵,植物?”他问。
“那是树,”老太太说,“外来的怪品种,树没活,但把地给顶起来了,应该砍了它。”
“交给我办。”还魂尸说。他沿着大树走了两圈,反复摸索一会儿,终于找到个趁手的位置。于是他弯下腰来,头冲下,双手环抱住树干。第一次用力,树干稍微动了一动;第二次用力,树开始摇摇晃晃;第三次用力,发出根茎断裂的哧啦哧啦声,大树竟被连根拔起,倒悬着栽倒在地,根部带出大块泥土,几根长长的蚯蚓掉在地上。
这声巨响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附近上坟的、瞧热闹、闲着没事的几个人全都看向这边,目瞪口呆。信光看也不看他们一眼,他用手把树根上的泥土拢起来,填回坑中,用脚踩平,形成了一个盆地般的小坑。老太太在旁边帮他拿着衣服,用手抚摸他后背浸满汗水的“H4004”黑色编号。这刺字是什么意思呢?她想,最好不要让别人看见。自老头去世之后,她一直没精打采、行迈靡靡,但几天来,失去多年的信心一并回到她的胸中,令她高兴地把头高高扬起,就像光彩万分地嫁到村子里时一样。信光干活很快,等两人回程时,身后已经跟了不少人,有人在录像,这是旧时代残存的习惯,网络被全面禁止后,录像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信光跟在母亲后面,走在小路上,黄泥从老太太鞋底掉了下来,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发现自己很喜欢土黄的颜色,这色彩就像黄昏,具有柔和的力量感。此刻正是黄昏时分,黄色微光浸润一切、使人通明。于是他感觉到力量澎湃汹涌,眼前所见之物不再是静止不动的画面,它们的命运像时间中的录影,缓慢但不可阻挡地呈现在眼前。大部分时候,画面是模模糊糊的,但却偶尔变得清晰起来。
前方,一条狗正趴在路边,爪子按住根泥呛呛的骨头。他们拖着人群浩浩荡荡经过时,它一动也没动,只是翻着眼球向上看。
“这动物,狗,快死了。”信光说,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过去。有的人蹲下,趴在狗的旁边看它喘气,更多的人跟着信光走了。走到第二条街道时,信光停下,看着房檐下坐着的一个农夫,大喊:
“快跑起来,事故!”
6
两天后,阵亡军人追思会在村公所举办。人们按翻书查来的旧时习俗,搭起一个巨大的灵棚,以灰毯为地、红白相间为顶,大棚两侧树长竿一十八根、秉烛三十六盏,场地中央摆几十把椅子,大家有的坐在椅子上,有的干脆席地而坐。为死者大发哀恸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几个女人在小声地哭,其他人都在谈话,亲属们近乎麻木,邻里也已习惯年轻人的死亡,他们一个接一个消失,就像是离家去上学、去工厂工作、去远赴黄金时代殖民的边疆,他们谈论这些就像在谈论一场宴会,有人中途离席,但不妨碍宴会的继续。老太太领着信光进来的时候,人已经把棚子坐满了。他俩走向侧面仅剩的几个空位,村民们转头望着他们,一下子安静下来。这寂静仅仅持续了片刻,一个小孩突然喊道:“怪物!妈妈,害怕!”旁边的母亲赶紧抱住了他,但孩子看起来并不怎么惧怕,他把头发埋在大人的怀抱里,偷眼向外看,瞳孔中倒映出还魂尸雪白的皮肤。
“这怪物怎么来了?”有人问。
“主任,把它赶走!”一个村民叫道。
“不是怪物,是我儿子!”老太太说,但似乎没有人听到。看不见的手捂住了所有人的耳朵。
“她有什么资格来?”有人大声喊。
“她儿子也是士兵,”公所主任说,“来就来吧。”
“他好胳膊好腿的,可我儿子呢?我儿子在哪里?”一个女人哭喊道。
“整个连队都完蛋啦,他却回来吃香喝辣,恬不知耻的胆小鬼!”
“他也经历了战争,不要难为他了。”主任说。
“这种怪物,应该回到前线,冲上去!为小伙子们报仇!”
“我不管!你们把我丈夫还回来!”一个年轻的寡妇大哭着冲向信光,却被会计拼命拦住了。
“冷静点儿!”会计说,“他不是人,是还魂尸,你懂吗?别跟他计较,他只是个还魂尸啊!”
“但他复活了!凭什么!凭什么我丈夫就不能复活!”
“我儿子是人。”老太太提高音量说,她用手紧紧揽住儿子的胳膊,“他跟你们一样吃饭,一样睡觉。”
“不一样!”一个孩子突然站起来,“我看过他拉屎,他的屎是深绿色,像果冻一样又黏又恶心。”
“你什么时候看到的?”老太太问。
“昨天,我趴在厕所看到的!辛也可以作证。”
“那你们就是偷窥者,是鬼鬼祟祟的小偷。”
“还魂尸才是小偷,”一个回来奔丧的年轻人站起来,“他偷走了村子的平静,让大家分裂、嫉妒,让失去亲人的人伤心疯狂,他不应该在这里,这里哪有他的位置!”
“我们还看见他偷吃鸡!他躲在厕所里,生吃了抓来的一只母鸡!”那个叫辛的小孩说。
“没有。”信光辩解道。
“还有,他来之后,村里的狗就不见了。”有人说。
“他拔了大伙儿祖坟的树,还顶翻了车子。”
“他前天诅咒了我丈夫!”一个女人歇斯底里起来,“他叫他小心出事故,结果他立马就被塌下的一块房顶砸伤了!”
“复活的魔鬼!叫他躲在家里,永远不要滚出屋子吧!”
听着这些,信光感觉周身的热量慢慢向眼睛积聚,他紧紧闭上着了火的眼睛,第一次体会到愤怒。如果可以剖开肚肠、掀开头颅检测,这种召之即来的情感足以证明他不是生化人、不是机器人、不是虚拟人,甚至不是阵亡将士的纪念品,而是个有情绪的、真正的人类。他想开口辩解,但审判席没有给他辩解的机会,自古以来,他们占着人数和道义的优势,从来不给别人机会。老太太紧拥着儿子,在嘈杂声中,还魂尸牢牢地抓住眼前的一柄长竿,愤怒地举过头顶。但他突然看到了未来,这个棚子的未来、这些人的命运。他看到自己将长杆插进女人的胸口,血就像山后的汩汩涌泉,她的血混合在十几个被彻底刺穿的人的血液中,铺满地面,形成暗红色的河流,蜿蜒地流到阵亡士兵的黑白相片前,涂满他们的军装和灰色的脸。棚子撕成了碎片,人们躺了一地,桌椅倾覆,有人像筷子般折断,有人头被砸扁,白色的脑浆流出来,掺杂在粉红色的泥水里。在这之后,他揽着母亲,一起步行回家,天上降下雨来……这多么像战场啊!他想起冰冷的机械把活人踩在轮下,脸皮从骨肉上分离,像大地长出的一张面具。这是永恒噩梦中挥之不去的残酷画面。他退缩了,默默地放下手中的长竿。眼前的景象如烟般散去。
母亲紧紧把住他的胳膊,指甲深深地嵌进肉里。她并未察觉到儿子预言的幻景,只是在不住地发抖。
“他要打人啊!”有人喊道,“他还想打人!”
“我们走。”母亲颤抖着说。
于是他揽着母亲的手,走出压抑的棚子,天上果真降下雨来。
7
信光已经好几天没有出门了。公所送来村民起草的《约法六章》后,母亲不再让他出去干活。这几天,他靠看影集度过了漫长的白日,影集是父亲的遗物,是老头在城里旧货市场淘到的,里面放着不知谁家的照片。一百多年前,城市里流行为死人拍生活照,摄影师用架子把尸体固定好,让他们或坐或立,眼睛黏成睁开的样子。他们只拍黑白照片,化妆师技术高超,以至于看客分不清谁是活人、谁是尸体。这应该算是还魂的古老形式——一种简陋的、平面的、复古的还魂。信光费力地辨认活人与死者的区别,但他失败了,他看不到照片中人物的未来,因为就现在而言,那些未来早已是过去。
咚咚,大门响了。信光预见出两个男人的模糊影子。他从凉爽的席子上站起来,回忆了《约法六章》的规定——第一,不准去阵亡军人家庭和追思会;第二,不准去祖坟;第三,不准破坏任何庄稼、植物、树木;第四,不准接近和伤害牲畜;第五,不准用不祥的言语诅咒;第六,天黑之前不准出门。他想了想,开门不违反规矩,他可以开门。
门外站着那个叫“会计”的人,旁边是个坐着机械轮椅、愁眉苦脸的老头儿,有个戴眼镜的姑娘推着他。会计冲信光笑了笑。
“怎么样,小伙子?适应村里的生活吗?”
“还好。”信光说。
“你觉得痛苦吗?”
“不。”信光回答。他感受到的更多是害怕。
“痛苦可以蒙蔽人,就像村子里那些人。”坐轮椅的老头开口说,“原谅他们吧,他们被痛苦和嫉妒捂住了眼睛。看到,却不能分辨;听到,却不敢相信;言语,却出口伤人。”
信光摇摇头。这时,老太太从后院钻出来,手里握着两根白色带须的萝卜。
“这是真正在土里长的萝卜吧,大娘?”会计说。
“当然!”老太太回答。
“很好,母子俩能一饱口福!”
“你们来做什么?”
“啊,这位是市里的技术专家,”会计指指坐轮椅的人,“前几天,腿不幸受伤啦!但他还有话要说,坚持来访。”
“您好!”老头儿抿着嘴唇笑笑,“我早该来的,遇上倒霉的车祸,住了几天院。”
“哦……不打紧吧?”
“没事,”专家说,“公司给治病、生活费、营养费、奖金、补贴,我还能说什么?只能拼命完成考核任务、感激涕零。为完成未竟的使命,我今天必须来,您就当走过场吧!”
老太太点点头。
“我们这次来,是问问生化人的事。”
“生化人?”
“就是你儿子。”会计插嘴说。
“什么儿子?”专家问。
“还魂尸啊,”会计说,“她儿子。”
“她儿子?你竟说生化人是她儿子?你最好清醒点儿,那只是团硅胶冻肉,把意识注入肉里,他从头到脚跟你一毛钱关系没有,他可不是人类。”老头说,“你们上次跟她说了什么?喷农药的小子说了什么?”
“没有,没有,就按指导手册讲的。他是个生化人,还魂尸!”
“嗯,别看他这样,屋子不敢出、什么都不懂、话都说不成句,未来可要仰仗他们!”老头说,拍着轮椅扶手,“他们不是人,强于人!你们要接受未来,就要先改变观念。”
姑娘俯下身,用手摸摸老头的脖颈,“你讲得太多啦。别忘了,我们是在偏远的村子里。”
“不用拍我,我可是有武器的人。”老头咧嘴笑笑,“你看过老电影吗?残疾人把枪藏在轮椅里,掏出来打天花板上的怪兽。看过吗?会计先生。”
会计脸上渗出汗珠来,从口袋掏出块皱巴巴的手绢擦擦脸。“没关系,您可以完全放心,村里没有危险!百分百放心!”
“让我问他几个问题。”
“好,快过来!信……你这还魂尸?别躲在门板后边。”会计喊道。
“白天不让我出家门。”信光说。
“别这么死板!”
“公所定了六条规矩。”老太太央求道,“不要为难他了。”
“只是因为这个吗?”老头说,“生化人,你过来,说实话。为什么不看我?”
“没有。”信光说。
“说实话!”
“……你会掏枪打我。”信光低声说。
老头笑笑,果然从背后摸出一把装有消音设备的小手枪。会计尖叫一声跳开。信光站在门边,面露犹豫。
“你为什么不躲开?”
信光眨眨眼,“场景变了,你不会真的开枪。”
老头看起来很高兴,他费力地扭过脖子,对姑娘说:“这个意识可以!成功了一半。我就说了,必须在生活中测试。”
“但他好像只能看到几秒钟?”
“别管时间长短,这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老头说完,把头转回来。“还魂尸!合同快到期了,好好和老太太享受最后的日子,我们下周一,就是后天,要把你带走了。你将回到属于你的地方。”
信光抬起头。“我哪儿也不去。”他说。
“别傻了。”老头说,“你以为你真的是儿子,她真的是母亲?没有我们的保养维护,你什么都不是。你现在只是个给人安慰的替代品,替一名工兵把生命延长了十几天,这就是你的价值。”
“只能再待这么两天吗?”老太太问。
“这已是极限啦。”姑娘接过话来,“为了这个实验、为了让你们延长这十几天,你知道我们正在损失多少钱吗?”
“那,你们会让他回到战场上去?”老太太颤抖着问。
“我本不想骗你,”老头把手上的枪支收回去,“你以为,他生来是为了做什么的?”
8
午后,村子里稀稀落落地下起冰雹来,大棚突然被砸坏了,人们冒雨解散了阵亡将士追思会。邮递员为信光家送来召回通知书,是军队里一个从未听过的番号。
吃完晚饭,他们谁也没开灯。在黑暗中,老太太和信光坐在一起,儿子像往常一样很少说话,盘腿望向北方。老太太不知那边有什么,她能看到的只有黑暗。她想,要是能找到个有趣的话题就好了,但就像所有的妈妈和儿子一样,很难找到共同的兴趣点。她轻轻摸着信光的手背,脉管在跳动,她发现自己越珍惜这个晚上,时间就过得越快。
“信光,你记得第一次坐旅行飞艇吗?”老太太问。
“不记得了。”
“你八岁的时候,把农药倒在培育牲口的池子里?”
“不记得。”信光答道。
“你十岁那年,从学校偷了一个报废的机器人,他本来是给跑道刷漆用的。”
信光摇摇头。
“你把机器人搬回家,在屋里放着。夜里,它自己动起来,在地上画了一个卖假钞的广告。”
“嗯。”信光吭了一声。他为自己的一无所知而感到羞愧,这也是他第一次体验到愧疚的感觉。母亲讲述的事情大概已随破损的芯片付之东流,又或者技术员太懒,没有把这些无关紧要的东西塞进他的脑袋。
老太太叹了几口气,没再为难他,只是拍了拍他的胳膊。信光想,自己的皮肤摸起来一定很凉,人类的皮肤是温暖的,而他却一直很冰凉。他闭上眼睛,学习人类的睡眠,这是他最早学会的东西,很简单——什么都不想,蜷缩在床上,像真正的人类蜷缩在充满温水的子宫里。他很快便睡着了,没有做梦。
清早,老太太做了六个菜,还打开了一瓶老头留下的浊酒。信光知道这是送行酒,他即将回到地狱中去。他踌躇着在小桌旁坐下,端起碗扒饭,眼前再次浮现出往日的景象,过去生活中的记忆全部消失了,战场的记忆却无比清晰地存在于脑海里。战车、炸弹、血雾、警报……还有那些已经永远消失的人。他们一个接一个出现,排队捧起桌上的酒杯向他致敬。信光看到了自己第一次从运输机下到兵营,第一次训练,第一次排雷,第一次踏上真正的战场,第一次从工兵变成侦察员,第一次扣动坚硬的扳机,子弹射入人体的感觉,密密交织的钢铁和射线,锈迹和血水……
他咕哝着嗓子,咽下最后一口饭,然后推开碗,拼命眨巴着眼睛,想看看自己明天会干什么,是回到实验室吗?还是直接上战场?他十分努力地去体验,但他却看不到,什么都看不到。他只看到母亲从后厨拿来了剪刀。
“先理个发吧。”老太太说。
信光坐到廊下,进入清晨肃穆的寂静里。这是他第一次被人修剪头发——至少是这具躯体的第一次。母亲理发的手艺很好,把他的头皮刮得干干净净。
“信光,你头顶有个大漩涡哦。”母亲说。
“是吗?”
“是啊。我问你,你小的时候,哭着要一架玩具战斗机,我一直没买,你会恨我吗?”
信光想了想,他不记得这件事,他什么都不记得。也许他根本不是什么信光,真的只是一具化学生产的还魂尸而已。
“不会。”他说。
“好了,躺下。躺在垫子上,对。”
信光顺从地躺好,老太太指挥他侧卧过去,摸了摸他,转身离开。
信光迷茫地躺在那里,听着老太太的脚步,愈来愈远、愈来愈远,又愈来愈近、愈来愈近,鼻子突然闻到了一股味道。他的头脑猛地张开,像撑开了一把接受讯号的雨伞。他用意识而不是眼睛,看见母亲正端着一盆深褐色的液体走来——那是醋的味道,他想起了溶解的感觉。他似乎不是第一次被溶解,上一次害怕得几乎不能动弹,模糊的人影把他从身体里拽出去,把另一个人安插进来。是信光进来了吗?离开的又是谁?雨伞的信号突然前所未见地强烈起来,他看到技术专家带了一队士兵过来,他夺门而出,杀得血流成河,敌人的痛苦呻吟几乎掩盖住老太太哭泣的声音。他将顺利跑出去,跑出村子,进入森林、河流、大漠,在大漠陷入流沙和永恒的孤独中去。当他最终走出来的时候,只有半截身子,他爬到废弃的中转站,爬到一百年前第一批殖民卫星离开地球的地方。他被治疗,被教化,成为半机器的野人,成为黑暗中畏畏缩缩的生物崇拜古神的载体。他们在崇拜人类,人类的形体和他一样,只是向来长了眼睛,却什么都看不到,拥有头脑,却什么都不去想,他看到面对愚昧,神们自己也缄口不言。
……他看见这一切,用脑子而不是眼睛。而眼睛看到的是母亲用颤动的手端着一大碗黑醋走过来。此刻他意念全开,身体灵活,完全可以一跃而出,逃离这间房子,冲破外面迫近的专家和士兵,获得同类不可企及的自由。但他却分毫都没有动弹,他继续躺着,等待母亲端着烧热的醋碗走到眼前。
“我绝不会再把你交到他们手里。”母亲说,眼泪不住地淌下来。
信光点点头,用万分之一秒时间思考自己的选择,然后慢慢关上他头脑里前无古人的意识之伞,闭上眼睛,等待接受母亲的热醋和爱意。战场的画面一下子变淡了,村子里的人们也不再成为困扰,他看到自己坐在庭院的屋檐下,在风中饮食,一只蝴蝶落在肩膀上——此刻,醋汁从高处颤抖着浇下来,有一些洒到了外面。当这些滚烫的液体灌入耳朵的时候,信光没有痛感,只感觉到暖和,世界在收缩,意识在慢慢固定中消散。他耳中听到的最后一个音符是海边的浪涛声,那年他只有七岁,乘坐旅行飞艇,第一次俯瞰大洋,海鸥在短小的舷翼侧面掠过,它们的翅膀反射着永不停止的太阳的光。

本文刊登于《科幻世界》2020年3期,获第32届中国科幻银河奖最佳短篇小说奖
最热文章

完美人生

隐形时代(下)(1)

隐形时代(上)(1)

【榕哥烙科】第537期:进化的速溶咖啡,如何越来越醇?

“瓷韵中秋,科技添彩”——2024年中国科技馆陶瓷主题中秋专场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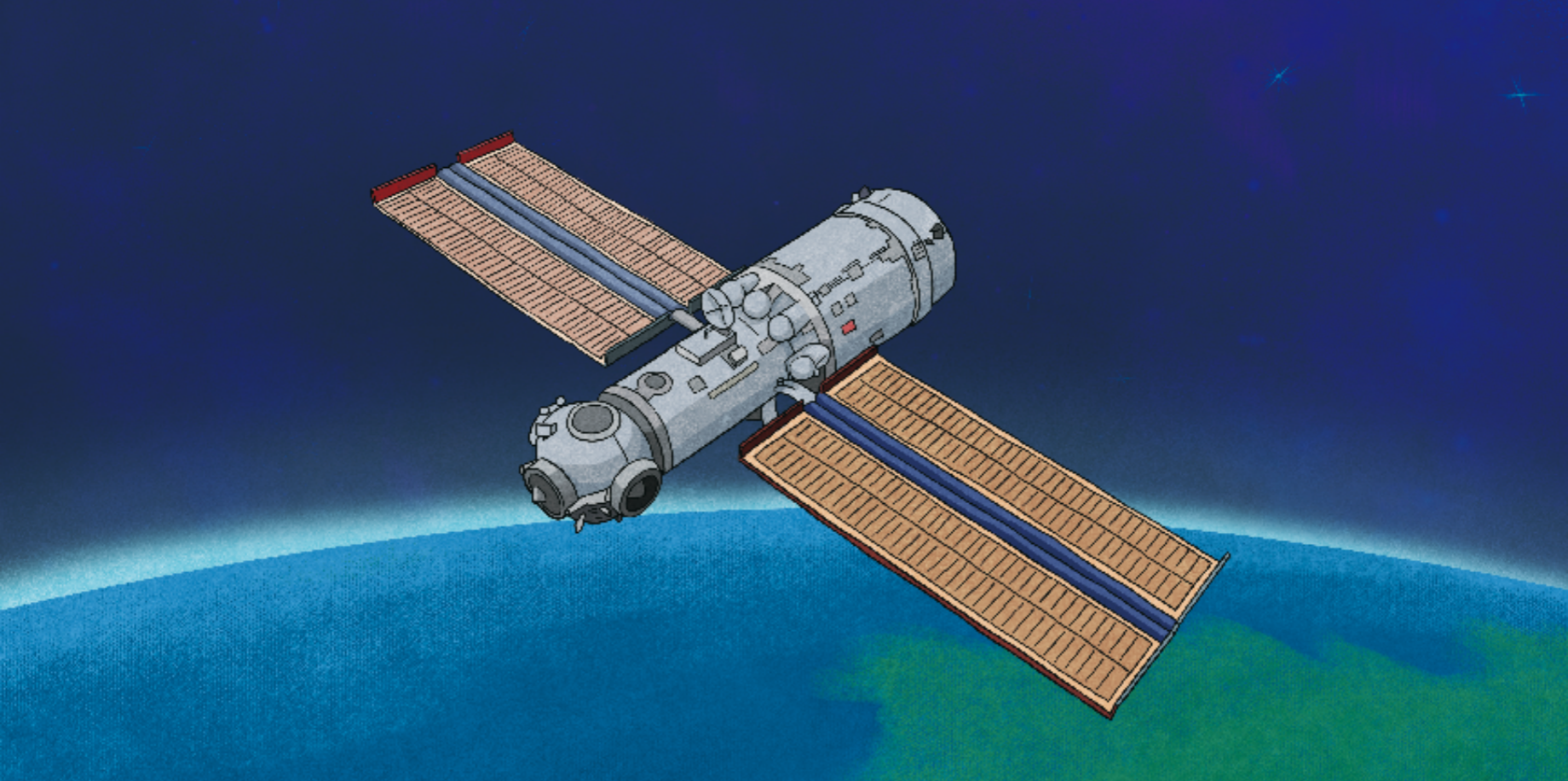
守时大神——空间冷原子钟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977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977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