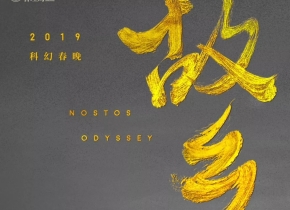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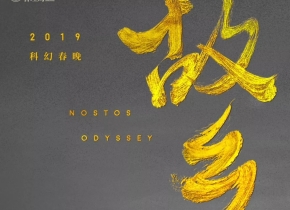


【加拿大】罗伯特·索耶/著
李毅/译
张晓雨/图
我先于我的同伴被带到未来。被传送之前我毫无知觉,耳膜里只感到一声爆裂,后来他们告诉我那是气压变化的缘故。到达21世纪后,他们扫描了我的大脑,为的是提取我的记忆,重建一座与我们在贝克大街221号B座完全一样的房子。甚至一些我无法记起的细节也被完整重构:贴着毛面纸的墙壁,壁炉前的熊皮地毯,柳条凳和扶手椅子,装煤的桶,甚至窗外的风景──连最细微的细节都完全一致。
我在未来时代碰到了一个自称麦克洛夫·福尔摩斯的男人。他声称与我的伙伴毫无关系,并发誓说这名字只是个巧合,不过,他承认研究我好友的演绎法是他的主要嗜好。我问他是否有个哥哥叫做歇洛克,可他的回答让我摸不着头脑,“我的父母受不了那种痛苦。”
不管怎样,这位麦克洛夫·福尔摩斯──一头红发的小个子,和我在两百年前认识的同名同姓的壮实男子有天渊之别──他希望在将福尔摩斯从过去弄到这里之前了解所有的细节。他说,天才离疯子只有一步之遥。对我来说,适应未来并非难事,但我的伙伴可能会被这种体验弄得失去理智。
麦克洛夫把福尔摩斯带来时做得非常隐秘,福尔摩斯刚一踏入真正的贝克大街221号的前门,便被即时传送到此处的虚拟实境中。我听到这位好友的声音从楼梯上传来,和平常一样问候虚拟的休斯顿夫人。他那双长腿,如往常一样,步子飞快,将他带上我们的这间陋室。
我期待着听到亲切的问候,或许包括一声热情的招呼“我亲爱的华生”,甚至可能是紧紧握手或者其他亲切举止。当然,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与福尔摩斯失踪三年后归来的那次不同,当时我以为他死了。不,这位我多年来一直在书中叙述他的冒险经历的同伴并没有意识到我们分开了多久,我的彻夜守候换来的只是一张紧绷的脸和心不在焉的点头。他坐了下来,伸手拿起晚报,片刻之后,他将报纸摔在桌上,“弄错了,华生!这份报纸我已经读过了。有今天的新报纸吗?”
于是,我只好接受命运的嘲弄,扮演起陌生的角色:我们的传统地位掉转过来,将由我来向福尔摩斯解释真相。
“福尔摩斯,我的好伙计,恐怕他们已经不再出版报纸了。”
他的长脸皱了起来,清澈的灰色瞳仁闪烁着光芒,“华生,我还以为像你这样在阿富汗待过很久的人不会被大太阳晒昏头脑哩。今天确实热得要命,可你的脑袋瓜不会这么轻易迷糊吧。”
“一点也没有,福尔摩斯,我向你保证。”我说,“我说的是真的。不过我得承认,当初他们这样告诉我时,我的反应和你完全一样。报纸到今天已经绝迹七十五年了。”
“七十五年?华生,这份《泰晤士报》是1899年8月14日出版的──就是昨天。”
“恐怕不是这样,福尔摩斯。今天是公元2096年6月5日。”
“两千──”
“20……”
“听上去挺荒谬的,我知道──”
“简直荒谬绝伦,华生。虽然我时常把你称作‘老伙计’,可怎么看你也不像250岁的样子吧。”
“或许,我不是向你解释这个问题的最佳人选。”我说。
“没错。”门外传来一个声音,“请原谅。”
福尔摩斯站起身来,“你是哪位?”
“我的名字是麦克洛夫·福尔摩斯。”
“冒牌货!”我的伙伴嚷道。
“绝非如此,我向你保证。”麦克洛夫说,“我承认不是你的哥哥,也不是第欧根尼俱乐部的常客,但我确实与他同名同姓。我是个科学家。我运用了某些科学定律将你从你的时代拖了出来,带到了我的现在。”
在认识他的这么多年里,我第一次从我的伙伴脸上看到了困惑的神色。“这是真的。”我对他说。
“但为什么?”福尔摩斯说,摊开长长的双臂,“假定这个疯狂的幻想是真实的──我此时并不同意──你为什么要绑架我和我的好友,华生医生?”
“因为,福尔摩斯,用你最喜欢的说法,游戏正在酝酿之中。”
“谋杀,是这样吗?”我问道,以为终于知道了被带到这里来的缘由。
“不是简单的谋杀,”麦克洛夫说,“远远不是。实际上,这是迄今为止人类遇到的最大谜团。失踪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上万亿。上万亿啊!”
“华生,”福尔摩斯说,“你肯定看出了这家伙是个疯子吧?你的药箱里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他吗?整个地球的人类还不到二十亿呢。”
“在你的时代,没错。”麦克洛夫说,“今天大概是八十亿。但我再重复一遍,有上万亿的生物失踪了。”
“啊哈,我终于明白了。”福尔摩斯说,当认为自己再次解开了谜团时,他的眼里闪烁着光芒。“我从《伦敦新闻画报》里读到过这些恐龙的故事,欧文教授把它们称为──来自过去的伟大生物,如今已全部灭绝了。你想让我解开它们的灭绝之谜。”
麦克洛夫摇摇头,“你应该看看莫里亚蒂教授的那本专著《小行星的撞击》。”他说道。
“我从不在无用的知识上浪费精神。”福尔摩斯简截地回答。
麦克洛夫耸了耸肩,“唔,在那本书里,莫里亚蒂相当聪明地猜中了恐龙的死因:一颗小行星坠入地球,扬起的尘土经年累月地遮蔽了阳光,造成了一场浩劫。在他提出这个合乎逻辑的假设约一个世纪后,我们在土层里找到了确凿的证据。因此,恐龙灭绝已经不再是个谜。目前这个谜比恐龙更加神秘莫测。”
“到底是什么?”福尔摩斯忿忿地问。
麦克洛夫示意福尔摩斯坐下,我的同伴坚持了一会,还是依言坐下了。“它被称为费米悖论,”麦克洛夫说,“以恩里科·费米命名。此人是二十世纪的一位意大利物理学家。你瞧,现在我们知道在宇宙中有无数行星,其中许多会产生智慧文明。通过所谓的‘德雷克方程’,我们可以从数学上证明这种可能性。一百五十年来,我们一直使用电波──我是指无线电──搜寻其他智慧种族发出的信息。但我们什么都没有找到──一无所获!于是费米悖论浮出水面:假定这个宇宙充满了生命,但那些异族人又在哪里?”
“异族人?”我说,“当然,他们通常都待在各自的国家。”
麦克洛夫微笑着,“亲爱的医生,自从你们的年代之后,这个字眼已经添加了更多含义。我说的异族人,指的是地球以外的人──居住在其他世界的智慧生物。”
“就像凡尔纳和威尔斯的科幻故事?”我问道,知道自己一定是满脸兴奋。
“甚至居住在我们的太阳系之外的世界。”麦克洛夫说。
福尔摩斯站起身来,“我对宇宙和其他世界一无所知。”他恼怒地说,“这些知识对我的职业没有实际用途。”
我点了点头,“初识福尔摩斯时,他连地球绕着太阳转都不知道。”我发出一声轻笑,“他以为刚好相反。”
麦克洛夫露出微笑,“我知道你们时代的局限性,歇洛克。”对这个过于亲密的称呼,我的朋友微微流露出厌恶。“但这只是知识上的缺陷,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弥补起来。”
“我不会让脑子里塞满不相干的知识。”福尔摩斯说,“我只记忆对工作有帮助的信息。例如,我可以分辨出140种不同的烟灰──”
“啊哈,那些知识你大可以扔掉了,福尔摩斯。”麦克洛夫说,“抽烟的人已经没有了。事实证明吸烟危害人体健康。”我朝福尔摩斯扫了一眼,我一直警告他吸烟是在慢性自杀。“而且,这么些年来,我们对大脑的结构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你担心记忆那些涉及文学、天文和哲学的知识会将别的信息挤出大脑,这是不成立的。人类大脑储存和检索信息的能力是无限的。”
“真的吗?”福尔摩斯说,显得相当震惊。
“千真万确。”
“所以你想让我投入到物理学、天文学和别的知识领域?”
“是的。”麦克洛夫说。
“以解决费米悖论?”
“正是如此!”
“可为什么找我?”
“因为这是个谜。而你,我亲爱的朋友,则是世上最出色的解谜高手。当今距离你的年代虽然已经过去二百多年,但仍旧找不到一个能与你匹敌的人。”
麦克洛夫可能看不出来,但福尔摩斯脸上隐藏的自豪瞒不过我的眼睛。然而,福尔摩斯却皱起了眉头,“得花好几年才能掌握让我解开谜团的知识吧。”
“不,不需要。”麦克洛夫摆了摆手,福尔摩斯那张杂乱的书桌上出现了一块玻璃,垂直地立着,旁边还有一个奇怪的金属碗,“自你们的时代之后,我们掌握知识的技巧有了极大的飞跃。我们可以直接将新知识载入你的大脑。”麦克洛夫走到桌旁,“这块玻璃片我们称为‘显示屏’。由你的声音来控制。只需向它提出问题,它就会按要求把信息以不同的主题显示出来。如果你认为某个主题对自己的学习有帮助,只需将这个金属罩放在头上,”他指了指那个金属碗,“说一句‘加载主题’,然后信息就会无缝地载入你大脑的神经中枢。一瞬间,你就掌握了该知识领域的一切资料,仿佛它们早就存贮在你的脑海似的。”
“真是难以置信!”福尔摩斯说,“然后呢?”
“然后,我亲爱的朋友,我希望你的演绎天才会引导你解开这个悖论──并最终揭示那些外星人到底怎么了!”
“华生!华生!”
我从梦中惊醒。福尔摩斯无法抗拒这种不费吹灰之力便掌握知识的新方法,他直到深夜还在摆弄个不停,但我肯定在椅子上睡着了。我意识到福尔摩斯终于给自己的烟瘾找到了替代品。过去,那些随时出现在手边的尼古丁,曾帮助他捱过没有案子时难忍的空虚。
“嗯?”我说,我的嗓子干得直冒烟,入睡时肯定没把嘴合上,“什么事?”
“华生,物理学比我想像的更加奇妙。听听这个,看它是否像我们以往碰到的案子一样引人入胜。”
我从椅子上站起,给自己倒了点雪利酒。我不在早上喝酒,但现在毕竟还算晚上,天还没亮呢。“我在听。”
“还记得苏门答腊岛的巨鼠案吗?那间至关重要的上锁密室?”
“我怎么会忘?”我说,脊柱上传来一阵寒栗,“要不是你准确的枪法,我的左腿早就成为老鼠的美餐了。”
“肯定是这样。”福尔摩斯说,“唔,现在我们考虑的是另一个不同的密室谜团,这是由一名奥地利物理学家埃尔温·薛定谔提出的。假定有一只猫被封在箱子里,箱子由完全不透明的材料制成,每一面都与外界隔绝,没有一丝缝隙,等箱子封上后,我们没有任何办法观察到那只猫。”
“太不人道了,”我说,“将一只可怜的小猫锁进箱里。”
“华生,你的同情心值得赞许。不过伙计,请抓住我话中的要点。假设更深一层,在这个箱里有个一触即发的装置,而这个装置控制着一罐毒气。如果触发器被碰到,毒气就会释放出来,那么这只猫就会死掉。”
“天哪!”我说,“太可恶了!”
“现在,华生,你告诉我:不把盒子打开,你能不能告诉我那只猫是死是活?”
“唔,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取决于触发器是否打开。”
“完全正确!”
“所以那只猫可能活着,也可能死了。”
“啊哈,我的朋友,我知道你是不会让我失望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但是错了,亲爱的华生,完全错了。”
“你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这只猫既不是活的,也不是死的。这是一只潜在的猫,一只未定的猫,这只猫的存在由可能性来决定。华生,它既不生也不死!直至有人打开盒子朝里看之前,那只猫的存在与否悬而未定。只有‘看’这个动作才迫使可能性得出一个结果。一旦你弄破封装朝里窥视,这只潜在的猫便物化成一只实在的猫。它的真实性是以观察结果为基础的。”
“这简直比那个与你哥哥同名的人所说的话更荒谬。”
“不,绝非如此。”福尔摩斯说,“这个世界正是这样。自我们的时代之后,他们对世界的认识有了极大提高,华生──飞跃式的提高!但是,即使在这么深奥的尖端物理领域,观察者的能力也是一切之中最重要的!”
我第二次醒来,听到福尔摩斯在大叫:“麦克洛夫!麦克洛夫!”
以前,我只偶尔听过他发出这样的叫喊,要不就是铁打般的身体背叛了他,得了发热症,要不就是受了他该死的针筒的影响。过了一会,我才意识到他不是在喊他真正的哥哥,而是朝着空气召唤另一个麦克洛夫·福尔摩斯,那个来自二十一世纪的奇人。片刻之后,他得到了回应:我们的房门打开了,一个红发的家伙走了进来。
“你好,歇洛克。”麦克洛夫说,“你找我?”
“没错。”福尔摩斯说,“我已经掌握了大量知识,不仅仅是物理学,还包括你为我和华生创建出这间房子的科技。”
麦克洛夫点点头,“我一直在追踪你涉猎的领域。我不得不说,这真是令人吃惊的选择。”
“或许是这样。”福尔摩斯说,“但我的方法是以弄清每一件细微事物为基础的。告诉我,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你是通过扫描华生的记忆,再利用──但愿我能理解这个术语──全息技术和微控力场虚拟出这些场景和他眼前的景象,因而重构了这间房子。”
“完全正确。”
“所以,你不止有重建我们的房子的能力,你还能虚拟出我们曾见过的一切事物。”
“说得没错。事实上,我甚至可以把你放进别人的记忆里。真的,我想或许你应该看看那个巨大无比的射电望远镜阵列,我们全靠它来侦听外星人的信息──”
“是的,是的,我敢肯定十分壮观。”福尔摩斯语带不屑,“但你能否重构华生在‘最后一案’一书中描述的犯罪现场?”
“你是说莱辛巴赫瀑布?”麦克洛夫一脸诧异,“天哪,是的,我可以做到。我本来以为那是你最不想重新体验的事。”
“你说对了!”福尔摩斯承认道,“你能做到吗?”
“当然。”
“请动手吧!”
于是福尔摩斯和我的大脑被扫描了一遍,很快,我们便发现自己置身于1891年5月的瑞士,回到了莫里亚蒂教授伏击我们的度假胜地。为我们重新设定的场景由迈林根村庄迷人的大英旅馆开始。和当年一样,虚拟出来的旅馆主人强烈建议我们不要错过莱辛巴赫瀑布美丽的景色。福尔摩斯和我动身前往莱辛巴赫瀑布,他拄着一根阿尔卑斯手杖。麦克洛夫──我现在已经明白了──则在远处以某种方式观察着一切。
“我不喜欢这样。”我对福尔摩斯说,“有过一次可怕的经历已经够糟了,除了在噩梦里,我不想再多体验一番。”
“华生,记得吗,对我来说这可是美好的回忆。除掉莫里亚蒂是我职业生涯的最高峰。那时我就跟你说过,现在我再重复一遍,只要能除掉这个罪犯中的拿破仑,即使以我的生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
一条泥泞的小径从林子里穿出,沿着瀑布绕了半圈,仿佛特意为这个景观提供完整的视角。融化的冰雪汇聚成流,形成碧绿冰冷的溪水,飞流直下,坠入如同黑夜般巨大、无底的岩石裂罅。激流溅起一串串水珠,汹涌的瀑布发出的巨响有如人类的悲鸣。
我们站了一会,望着脚下的深潭,福尔摩斯陷入忘我的沉思。然后,他指了指前方泥泞小径的深处。“注意,亲爱的华生,”他大声说道,以压过湍流的巨响,“那条泥泞小径的尽头是一道岩壁。”我点了点头。他转到另一个方向,“我们前来的道路是惟一离开的退路:这儿只有一个出口,同时也是惟一的入口。”
我再次点了点头。和上次我们来到这个命运的转折点一样,一名瑞士男孩沿着小径跑来,手里拿着一封写着我名字的信,上面印着大英旅馆的标记。当然,我知道信里说的什么:住在旅馆里的一名英国女士因病突然出血不止。她命在旦夕,但如果有一名英国医生从旁照料,必定能减轻她的痛苦。信中请求我立即返回。
“这封信是个藉口,”我说,朝福尔摩斯转过身,“是的,上次我被它骗过了。不过,正如你之后在留给我的信中承认,你从一开始便怀疑它是莫里亚蒂的阴谋。”我们说话时,那名瑞士男孩凝固了,纹丝不动,似乎在观察一切的麦克洛夫用什么方法将他定住了,以便福尔摩斯和我讨论。“我不会再离开你,福尔摩斯,让你陷入生命危险。”
福尔摩斯举起一只手,“华生,与以往一样,你的高尚值得赞赏,但别忘了这只是个虚拟实境。如果能像上次那么做,你将给我极大的帮助。不过,你无需再经历来回大英旅馆路程中的艰辛。你只要回到遇上黑衣人的地点,等上一刻钟,然后返回这里就行。”
“多谢你指出这一点。”我说,“现在的我比那时年长了八岁,三小时来回路程恐怕会要了我的老命。”
“没错。”福尔摩斯说,“我们可能都过了年富力强的岁数。现在,请照我说的做吧。”
“我会的,当然。”我说,“但我必须承认,我不明白这么做有什么用处。这个二十一世纪的麦克洛夫要你解决的是一道物理难题:失踪的外星人。为什么要来这里?”
“我们在这儿,”福尔摩斯说,“是因为我已经解开了谜团!相信我,华生。相信我,让我们再次重历那可怕的一天吧──1891年5月4日。”
于是,我离开我的伙伴,对他的打算一无所知。沿路返回大英旅店时,我迎面碰到一个匆忙赶路的男人。
在第一次的可怕经历里,我不知道他是谁,但这次我认出他正是莫里亚蒂教授:高个子,一身黑衣,前额外凸,瘦削的体形在绿荫的衬托下显得相当突出。我让这个虚拟人从身旁通过,按福尔摩斯的吩咐等了十五分钟,然后返回瀑布。
当我到达时,我看到福尔摩斯的阿尔卑斯手杖倚着一块岩石,湍流不断溅在通往瀑布的黑土小径上。在泥地里,我看到两行指向瀑布的脚印,但没有掉转的迹象。眼前可怕的情景与多年前一模一样。
“欢迎回来,华生!”
我转过身。福尔摩斯靠在一棵树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福尔摩斯!”我惊叫着,“你怎能离开瀑布而不留下脚印?”
“记得吗,亲爱的华生,除了活生生的你和我,其他一切全是虚拟。我叫麦克洛夫不要留下我的足迹,就这么简单。”他示范地来回走了几步。他的脚下没有留下痕迹,地上的小草也没有被压弯。“当然,在莫里亚蒂和我进行生死决斗之前,我还叫他定住莫里亚蒂,像早些时候他定住那个瑞士小男孩一样。”
“太神奇了。”我说。
“没错。现在,考虑一下你面前的景象。你见到了什么?”
“与我在那个可怕的日子里见到的一样,我以为你死了:两行脚印指向瀑布,没有返回的踪迹。”
福尔摩斯大声喊道:“没错!”声音足以与瀑布的怒吼相抗衡。“其中一行脚印你知道是我的,而另一行,你认为属于那个穿黑衣服的英国男人──罪犯中的拿破仑!”
“是的。”
“看到两行脚印走向瀑布,却没有返回的痕迹,于是你冲向瀑布边,然后发现了──什么?”
“我在倾泻着急流的悬崖边发现了打斗的痕迹。”
“因此你得出什么结论?”
“你和莫里亚蒂坠下了瀑布,在生死决斗中双双丧命。”
“完全正确,华生!在这种情形下,我自己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不过,谢天谢地,事实证明我的结论是错误的。”
“是吗,现在还这么认为?”
“你怎么了?这是当然。你出现在这儿就是证明。”
“或许吧。”福尔摩斯说,“但我不这么认为。想一想,华生!你处于现场,你见到了发生的一切。而且,这三年来──三年啊,老兄!──你一直相信我已经死了。那时我们成为朋友和同伴已有整整十年。你所认识的福尔摩斯会音讯全无,任你伤心如此之久吗?当然,你必定清楚,我对你和我的哥哥麦克洛夫同样信任。后来我告诉过你,他是惟一知道我仍然在世的人。”
“唔,”我说,“既然说起这个,我当时确实有点生气。但你回来之后向我解释了原因。”
“你从悲痛中恢复了,华生,对我来说这是个安慰。但我想,恐怕是你自己而不是我抚慰了你的心。”
“啊?”
“你看到了我死亡的明显证据,而且深信不疑,用文彩斐然的笔法在探案系列中记之为《最后一案》。”
“是的,没错。我平生就数那一次最难下笔。”
“那本书出版时,你的读者有什么反应?”
我摇摇头,回忆着,“完全出乎意料。”我说,“我以为会有许多悼念你的礼貌的评论,因为你的探案故事一直大受欢迎。可我收到的大部分来信都是愤怒和不满,大家都要求听到你更多的历险传奇。”
“当然,你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你看到我死了。”
“没错。这件事做得实在不怎么样,我不得不说,你这种行为十分古怪。”
“但毫无疑问,事情很快就平息下来了。”福尔摩斯说。
“你知道得很清楚,完全不是这样。我告诉过你,除了谩骂的来信,无论我去哪里,都饱受批评,一直持续数年之久。实际上,当时我正准备撰写一本过去漏掉的你的探案历险。不是出于兴趣,仅仅是为了平息那场风波,就在这时,让我惊喜交集的是──”
“让你惊喜交集的是,在失踪了差一个月三年之后,我重新出现在你的诊室里,乔装打扮,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装成一名衣着不整的藏书者。很快,你就出版了最新的探案传奇,记述那个臭名昭著的案子:塞巴斯蒂安·莫安中校及其牺牲品,受人尊敬的罗纳德·阿戴尔。”
“是的,”我说,“真是让人惊喜不已。”
“可是华生,让我们再次分析一下我在1891年5月4日死亡的有关事实。你,场景的观察者,看到了确凿的证据,而且正如你在《最后一案》里的叙述,许多破案专家在瀑布的边缘进行了详尽的勘探,他们也得出了与你完全相同的结论──莫里亚蒂和我坠入深潭,双双丧命。”
“可事实证明那个结论是错误的。”
福尔摩斯意味深长地笑了笑,“不,我亲爱的华生,事实只证明了,这个事件是不可接受的──不被你忠实的读者所认可。这正是整个问题的关键所在。还记得薛定谔封在箱子里的猫吗?莫里亚蒂和我在瀑布旁的出现就是非常相似的情景:他和我沿着小径走进一条独头路,我们的脚印在松软的泥地上留下压痕。在这一点上只有两种可能的结果:我不是安全逃脱,就是命丧当场。那里没有其他出路,只能沿着同一条小径从瀑布返回。直到有人前来并看到我是否重新出现在小径上,其结果是悬而未决的。我既是活的,又是死的──一个可能性的合集。但当你到达后,种种可能性便坍塌为单一的事实。你没有看到从瀑布返回的脚印──意味着莫里亚蒂和我在搏斗中跌下悬崖,最后坠入冰冷的湍流。正是你那个‘看’的举止迫使可能性得出一个解。换句话说,我亲爱的好友,是你杀了我。”
我的心脏在胸膛里怦怦直跳,“听我说,福尔摩斯,没有什么比看到你还活着更令我感到欣慰!”
“我对此毫不怀疑,华生。但你只能见到一种可能。你无法二者皆得。根据你目睹的情况,你报告了自己的发现:先是向瑞士警方,然后是《日内瓦月刊》的记者,最后再写入书中。”
我点了点头。
“不过,这里有个问题是薛定谔在提出将猫密封在箱里的实验时没有考虑过的:假定你打开箱子,发现小猫死了,之后你将它的死讯告诉了你的邻居──他却拒绝相信。那么,如果你再回去察看盒子,会发生什么事?”
“嗯,那只猫当然还是死的。”
“有可能。但若是有几千──不,几百万人!──拒绝相信最初那个观察者得出的结论呢?如果他们一致否认事实,那时会怎样,华生?”
“我──我不知道。”
“在他们顽固的意愿下,他们重组了现实,华生!真相被假想替代了。他们希望那只猫复活。不仅如此,他们还试图相信那只猫根本没有死!”
“于是──”
“于是,这个世界──本来应该是个实有的现实──现在却被推回到悬而未决、不确定与漂浮的状态。作为第一个到达莱辛巴赫瀑布的观察者,你的解释本来应该被他人优先采纳。然而人类的顽固实在令人惊讶,华生。通过彻底的否定,拒绝相信他们所听到的一切,这个世界重新归于悬而未决的波动状态。我们存在于悬浮状态──直到今天,整个世界都处于悬浮状态──因为你在莱辛巴赫的观察,与人们希望你作出的结论无法调和。”
“可这太荒谬了,福尔摩斯!”
“排除不可能发生的事,华生,剩下的不管是什么,不管如何不可思议,也必定是真相。之后,我想到了那个有如上帝化身的麦克洛夫要我解开的谜团──费米悖论。那些外星人到底在哪里?”
“你是说你已经解开了这个谜?”
“确实如此。想一想,人类通过什么方式来寻找外星人?”
“利用无线电,我想──他们试图侦听外星人在电波里的交谈。”
“没错!那么我是什么时候死而复生的,华生?”
“1894年的4月。”
“而那个意大利天才发明家——古利莫·马可尼,什么时候发明了无线电?”
“我不知道。”
“是1895年,亲爱的华生。接下来的一年!在人类发明无线电后的历史长河里,我们的整个世界都处于潜在的游移状态!一个尚未坍塌、仍处于不断波动的状态中。各种可能性悬而未决!”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外星人始终存在,华生──消失的不是他们,而是我们!我们的世界和宇宙的其余部分失去了同步。由于不愿接受那个令人伤痛的事实,我们让自己退回了潜在的状态。”
我一直把这位伙伴视为一个有高尚情操的人,然而这么做的代价实在太大。“你是说,福尔摩斯,当前这个世界悬而未决的状态与你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
“没错!你的读者不同意我就此死去,尽管这么一来我实现了自己的梦想──除掉莫里亚蒂。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观察者对他的观察结果失去了控制!倘若这世上有一件事是我毕生所追求的(你在《空房子》一案里记叙了我荒唐可笑的复活,我指的是自己在此之前的生命),那就是理性!逻辑!以及忠于事实!然而人类却放弃了它。整个世界陷入了紊乱,华生。因为他们的放弃,我们这才切断了与其他文明的联系。你说过对我的复生感到无比欣喜,但如果人们真的理解我,理解我毕生的追求,他们就会知道,对我来说,真正的敬意或许就是接受事实!惟一的、真正的答案就是接受我死去的事实。”
麦克洛夫把我们送回过去,但不是他把我们掳走的1899年。在福尔摩斯的要求下,他把我们送回到八年前,也就是1891年的5月。当然,那里已经存在着年轻版的“我们”,但麦克洛夫将我们作了交换,将“年轻版”带到了未来,他们将在从我和福尔摩斯大脑中提取的虚拟实景里度过余生。当然,我们两人比第一次与莫里亚蒂相遇时年长了八年,不过我们在瑞士没有熟人,因此不会有人留意到我们已显苍老的面孔。
我发现自己第三次出现在莱辛巴赫瀑布,还是在决定性的同一天。然而,这一次和头一次相同,与第二次迥异,它是真实的。
我看到瑞士男孩正朝我们走来,我的心脏剧烈跳动。我朝福尔摩斯转过身,说:“我不能离开你。”
“不,你能做到,华生。你也会这么做的,因为在你和我两人的游戏中,你从来没有拒绝配合我。我相信你会陪我玩到底的。”他顿了顿,这才继续开口,或许是有一点伤感吧,“我可以揭露真相,华生,但我不能改变它们。”之后,他神情庄重地向我伸出手。我用双手紧紧握住。这时,莫里亚蒂雇请的男孩来到我们面前。我自动跳入圈套,让福尔摩斯独自留在瀑布边。我踏上回程,下了最大决心不准自己转头回望,赶回去治疗大英旅馆那个子虚乌有的病人。在回程中,我碰到了从另一个方向走来的莫里亚蒂。我只有尽量克制自己,才没有拔出手枪,将这名恶棍送上西天。因为我知道,如果剥夺了福尔摩斯与莫里亚蒂对决的机会,他一定会将这种行为视作不可宽恕的背叛。
大英旅馆的回程花了一个小时。在那里我扮演着询问生病的英国女人的一幕。旅馆的主人斯特勒老头露出一脸惊讶──这我早就知道。我的“表演”或许显得心不在焉,因为这个角色我已演过一次。很快我便开始返回。上山的路程花了两个多小时,坦白地说,到达山顶时我已经筋疲力尽,尽管在激流的咆哮下,我几乎听不到自己的气喘声。
我再一次看到两行走向悬崖的脚印,没有掉转的痕迹。我也发现了福尔摩斯的阿尔卑斯手杖,与头一次那样,旁边压着一张他写给我的字条。里面的内容与原来一样,解释了他将要和莫里亚蒂进行生死决斗,但莫里亚蒂允诺他留下最后的字句。然而,字条的结尾留下了一段与原来版本不同的附言:我亲爱的华生(上面写道),请不要在公众压力面前退缩,坚持你作为观察者的能力。这样做就是对我的死亡的最大尊重。不管他人怎么想,让我死去吧。
我返回伦敦,与妻子玛丽分别几个月后的重逢暂时抚平了我对失去福尔摩斯的伤痛。我解释说我略显苍老的面容是受福尔摩斯的死讯的震惊所致。第二年,完全不差分毫,马可尼真的发明了无线电。劝说我延续福尔摩斯传奇的意见继续纷沓而至。尽管我的生命中失去了他是个沉重打击,作为我所认识的最好、最睿智的朋友,没有什么比再次听到他的声音更能让我感到欣慰。我也曾几乎经受不住诱惑,放弃自己在莱辛巴赫的观察所见,但最终我还是不为所动,坚持了自己的观察所见。
1907年6月下旬,我从《泰晤士报》上读到一条消息:我们接到了牵牛星上传来的智慧生物的无线电讯号。那一天,全世界都在庆祝、狂欢,只有我泪如泉涌,怀着特殊的敬意,为我的好友──已故的歇洛克·福尔摩斯举杯致敬。
每日荐书

去年年前,我最后一次见小玲,是在我导......

莫名的,在一片沉默之中,我突然接收到......
最热文章

人工智能写科幻小说,和作家写科幻小说有什么不一样?

德国概念设计师Paul Siedler的场景创作,宏大气派。

《静音》是一部 Netflix 电影。尽管 Netflix 过去一年在原创电影上的表现并不如预期,但是《静音》仍让人颇为期待

最近,美国最大的经济研究机构——全国经济研究所(NBER,全美超过一半的诺奖经济学得主都曾是该机构的成员)发布了一份报告,全面分析了 1990 到 2007 年的劳动力市场情况。\n

J·J·艾布拉姆斯显然有很多科洛弗电影在他那神秘的盒子里。\n

我们都知道,到处都在重启;我们也知道,如果有钱,啥都能重启。所以,会不会被重启算不上是个问题,只能问什么时候会被重启。自然而然地,世界各地的各种重启现象衍生出了一个有趣的猜猜游戏:哪一部老作品会是下一个接受这种待遇的?\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