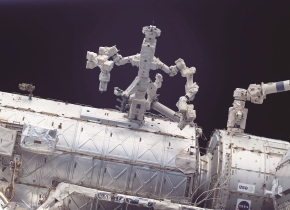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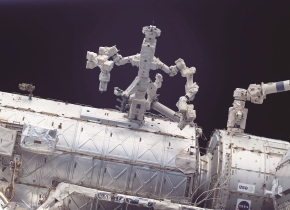

文 / 汤志诚
城市,人类文明的结晶。无数标新立异的高耸大楼,错综复杂的立交桥,与四通八达的地下隧道交织出了人类文明最繁华的景象。越发完善的管网系统与电缆将整个城市连成一个井井有条的庞大有机体。人类创造了城市为自己服务,而如今,日益详细化的城市自动化设施已逐渐取代了原本属于人类的职能。
城市,就如一个巨大的托盘,承载着人类所发展出的一切机械化文明。便捷的交通体系懒惰着我们的双腿,强有力的工程机器解放了我们的双臂,发达的信息捕捉与通讯设备是我们眼耳口鼻的延伸。人们足不出户便能打理外界一切事务早已不是天方夜谭。
或许,无数的科幻小说家构想的高度发达的机械文明,未必只能在那遥远的外太空得以一寻。倘若我们将自身的城市体系推向极致,那么可以设想一下,一个完全笼罩在电子机械架构中的城市会是怎样一番光景。
会爬动的模块单元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自古以来,“建筑绝不会自己长腿跑路”是每一个地球人心中的常识。但这样的常识在行军蚁的社会中可就不怎么适用了。这些习惯于四处游猎的凶悍小蚂蚁可不会耗费大量的精力在某个固定的场所修建自己的巢穴。为了解决安营扎寨的问题,行军蚁选择了用工蚁们的身体首尾衔接,构筑起一幢肉体蚁巢,将重要的蚁后、蚁卵、幼虫等庇护其中,而待到蚂蚁大军再度出征之时,这些建筑的“砖瓦”便又自动解体,成为了一辆辆“运输车”。
这种犹如液态金属机器人一般,在“流体”与“固体”之间自由切换的构造模式,恐怕是任何一个城市规划师所梦寐以求的了。
不用再担心一时的布局失误会导致后续工程的难度增加;也不用烦心随着城市需求的增长,拆陈革新的成本令人无法承受;而那些大意不得的贵重建筑的保护与挪位问题,也将不再是困扰专家们的技术大难题。
我们的城市将是“活的”!
在机械化城市的时代,“和尚”与“庙”不再是两个截然分离的概念。不同于当今城市中那些由钢筋混凝土简单搭建而成的“人造洞穴”,移动模块建筑将由诸多相对独立的“单元房”组成。这些严格按照统一规格制造的单元房就宛如一只只长方体的大毛虫,它们头尾衔接,在马路中央排列成一字长蛇阵,有条不紊地前进。长方形躯体的两侧下方,两排细小的滑轮与爪钩就如毛虫短小的腿脚,推动着单元房朝着目标位置进发。
在目标工地上,先一步到达的地下管网与基座支架部分已然自动组装完毕。“毛虫”们纷纷从队列中离散而出。先头的单元房爬上了地基,扫描着身下地基中的位置芯片,并对比着自身数据库中的电子蓝图,标注属于自己的位置。一旦定位准确,身下两侧的滑轮便紧紧抱死,爪钩也一一伸出,将自己扣锁在原位,单元房便这样将自身与基座牢牢地固定在了一起。紧接着,水电光缆等插槽也随之弹出,精确地与基座接口对接,原本分离的单元房们此时紧密地连接为了一个整体。
后续的单元房们也没有停歇,它们的爪钩抓着已经组装完毕的底层同伴们体侧的钢轨,犹如攀爬悬崖一般,朝着更高一层楼攀登了上去……于是乎,就这样一层又一层,这些活动的房间们自觉地让自己如同积木一般搭建了起来。无数的单元房在大厦的外侧蠕动着,那前赴后继的景象宛如蜡烛滴泪的快镜头播放,硬生生地从平地上“涌”起了一幢雄伟的大厦!直至整个队列中的末尾成员爬上了建筑的最尖端,构成了屋顶天台,一套完整的建造过程才算是正式结束。
这时候,所有的单元房都安静了下来。毛毛虫大军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幢珊瑚礁似的静态建筑物。基座层以上的单元房们通过外接插槽的对接,并入了水电与光缆的网络,共享着资源。
如果没有意外发生,建筑将保持着这样的组合姿态直到下一次的转址大迁徙。不过有些时候,部分单元房也会独自从自己占据的位置中抽离出来,在建筑的外墙表面爬动两圈,直到溜达够了再返回那个属于自己的空位。
这可不是啥程序错误。原来,为了保证每一个单元房在需要的时刻能够拥有无障碍的行动能力,长期处于静止状态的单元房必须定期检查自身的机动装置的功能有效性。每次从建筑物主体中抽出少数单元房并不会对建筑整体的稳定性产生太大的影响,却能给予解放而出的单元房以自检、养护、维修老化零件的机会。
倘若某间单元房果真因为事故而丧失了行动力,那也不打紧。回旋于城市低空中的救援飞艇在得到求助申请之后便会及时赶到,它们下垂的爪钩就如同黄蜂的六肢,将“臃肿的瘫痪毛虫”从它的坑位中切割拖拽而出,抱在身下,运往维修中心。
此种方法同样适用于城市建筑穿越复杂地形时候的快速搬迁。当大型飞艇停泊于建筑物上空时,位于最上层的单元房首先松开了爪钩,转而与大型飞艇腹部的钢轨衔接,然后爬动到里侧的停泊位,下一个单元房尾随其后……直至一长串的单元房密密麻麻地悬挂满大型飞艇的腹部,飞艇这才腾空而起,带着一肚子的小房间,飞跃过峡谷深沟、高山丘陵、江河海湾,或者干脆是另一个拥挤的城市,直达搬迁的新址。
鹦鹉螺大脑
或许,在看完上述文字后,读者们会产生这么个疑问——当一间单元房开始垂直在墙面上爬上爬下的时候,其内部摆放的家具岂不是稀里哗啦地凌乱了一地?这桌子椅子,彩电冰箱,锅碗瓢盆什么的,可不就如同经历了一场大地震,一片狼藉?
在这里,笔者有必要介绍一下机械化时代,我们人类,以及人类必备的生活用品将产生何等的剧变。
如本文的开头所述,城市是个承载机械文明的大托盘,而各种各样的辅助机械正越来越多地取代着人类的职能。在机械化时代,这一取代过程终于完成了最后的蜕变——传统意义上的人体消失了!在人类的繁衍过程中,身体各部分组织将不再发育,只剩下神经网络异常活跃地增生着。
在每一间单元房的中央,一只鹦鹉螺外壳般的容器便是容纳人类神经组织的核心系统。螺圈状的内壁布满了小肠绒毛状的褶皱,每一层褶皱之上,都密密麻麻地覆盖着无数形如花椰菜的轴突。绵延起伏的神经细胞组成的网络便如一张摊开的复合层蜘蛛网,披覆在这些微观的山林之中。
没错,这便是我们的大脑,不再是那蜗居颅腔中的球形。此时的人类大脑呈现出又薄又大的网膜状结构,与鹦鹉螺壳紧密帖服在了一起。花椰菜似的轴突既是神经细胞生长的附着点,也是信号传送的微观终端末梢。神经细胞之间的信号传输将直接通过这些末梢,与鹦鹉螺壳上的外部总线相连,以光速传导。因而,比起攒成一个球形,内膜式的大脑能更大面积地与机械媒介相接触,使之成为更实效的选择。
鹦鹉螺壳的周围,层层叠叠的外存储器以及电子信息处理器,辅助着人类大脑处理着海量信息的机械化运算与储存工作,这让人类的大脑可以腾出时间,专心处理“自由数据模拟组合”之类标志着人类“灵魂”的运算。
如此一来,家具搬运问题便自动迎刃而解。是的,机械化时代的人类将不需要桌椅床铺,也没有彩电冰箱。比起传统意义上的“房间”,单元房的内部构造更类似一台巨大的电脑机箱,鹦鹉螺脑室就是那核心的CPU。每一个零件稳稳地固定在六面墙壁上,屋主的感知也由此与房间联通在了一起。
形形色色的特异建筑
一座功能健全的城市可不能只有居民楼。机械化时代的大都市中,人们不再需要体育馆,不再修建音乐厅,然而这并不意味有着特殊功能的建筑物将从城市中消失。
在鳞次栉比的楼宇之间,你可以看到那一幢幢直刺云霄的尖塔。它们是如此高大,仿佛是灌木丛中散生的塔松。
唤雷塔——机械城中的综合性骨干建筑,身兼雷达、电台、能源供给等数职。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功能,也是其名字的由来。唤雷为电,这个古人们曾寄托以神话的梦想,在机械城中将得以实现。
天空中聚集起了那藏青色的厚重积雨云,电光闪闪,闷雷阵阵,大自然豪迈地挥洒着它那过剩的能量。一道道闪电毫不吝啬地贯穿空气,投向大地。人们在感叹自然的威武的同时,却也叹息自己无福消受那充沛的能源。
但在机械城中,你将看到另外一幅光景。
每当积雨云飘过城市的上空,距离云层最近的那幢唤雷塔便开始行动!数百条蛛丝般的导线从塔尖射出,随风飘摇直上。它们如同柔软的水母触手,用那锋锐的针尖刺破肥厚的积雨云,细密的电流顺着导线倾泻直下,犹如一条条钻破巢穴的小蛇,争先恐后地涌向了A字形的唤雷塔。此时的积雨云中并未积累够足以击破大气的强势电压,因而这些被人工干预而提前释放的电荷并不足以对唤雷塔的瞬间蓄电能力产生过大的压力。一场孕育中的狂雷怒闪就这样被化解吸收于细润无声之中。
唤雷塔之间由发达的电网相连。从天空中吸收到的能源被均匀地分配到了城市的各个角落,与其他途径产生的电能一同被储备着,供给着整个城市的消耗。
在城市的高层建筑之间,错综复杂的钢缆如树杈间隙浓密的蛛网、藤蔓,将各幢高层建筑牵挂在了一起。守护蛛锁——机械城中的另一大标志性景观。或许以人类的审美来看,这些遮天蔽日的城市蜘蛛网实在是有碍观瞻。但对于机械城而言,它们却是最简单实用的保护神。这些粗细有秩、疏密相间的网锁时时刻刻承受着城市上空猛烈的高楼风。激烈的空气对流穿过蛛网的网眼,经弹性舒张的网丝层层过滤,最终以温和的形态降临地面。在此过程中,网丝的伸张与收缩引起的震颤牵动着缆线上的磁感装置,在产生阻力的同时,将这些零散的破坏性能量转换为了电力。
有了守护蛛锁,沿海地区的机械城便可抵御台风的侵袭。而在地震高发区的城市,守护蛛锁同样可以吸收地震波对高层建筑的冲击。
对任何城市而言,一支四处游走的城市修补匠小队都是必不可少的。
当城市的某个部分因为战争或者猛烈的突发性自然灾害而遭到破坏,大大小小的机械蜂蚁便从地下的休眠场中紧急出动。大型机械蜂蚁在马路上奔驰着,以强有力的前肢搬开灾难后的各种残骸废墟,并将其丢入敞开的“粉碎窨井”。血盆大口一般的窨井将这些垃圾初步分解后,推送到地底管网,运回城市地下层的垃圾回收站。小型钢铁蜂蚁则顺着守护蛛锁,如特种兵一般,直接空降到了受灾严重的建筑层面,凭借它小巧轻盈的躯体,钻进单元房,抢救出重要的鹦鹉螺大脑。飞行系蜂蚁升上了高空,与救援飞艇配合着,盘旋在城市的各个区域,第一时间传回清晰的动态影像,以供城市管理者决策。待到修复完成,这些在非常时刻才会出现的机械蜂蚁便重新蛰伏到了地下,机械城再度恢复到了只有电信号频繁往来的宁静状态。
【 责任编辑:刘维佳 】
本文来自:最热文章

人工智能写科幻小说,和作家写科幻小说有什么不一样?

德国概念设计师Paul Siedler的场景创作,宏大气派。

《静音》是一部 Netflix 电影。尽管 Netflix 过去一年在原创电影上的表现并不如预期,但是《静音》仍让人颇为期待

最近,美国最大的经济研究机构——全国经济研究所(NBER,全美超过一半的诺奖经济学得主都曾是该机构的成员)发布了一份报告,全面分析了 1990 到 2007 年的劳动力市场情况。\n

坏机器人制片公司最新的一部电影名为《霸主》(overlord),背景设置在二战时期,很可能是一部在半遮半掩中秘密制作的科洛弗电影系列。

我们都知道,到处都在重启;我们也知道,如果有钱,啥都能重启。所以,会不会被重启算不上是个问题,只能问什么时候会被重启。自然而然地,世界各地的各种重启现象衍生出了一个有趣的猜猜游戏:哪一部老作品会是下一个接受这种待遇的?\n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977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977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