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_ 杨晚晴 图 _ 张旭东
DAY 234
“在我们的婚姻和史蒂夫之间做出一个选择,”我拼凑出一个笑容,“我想这对你来说一定很难吧,安娜?”
妻子的脸色变得惨白。“肖,”她双臂环抱,“有些事情,我们不该当着——”
“凯文,”我没有理会她,而是将身体探向男孩儿,“你听说过电车难题吗?”
男孩儿将目光投向与他同样茫然的母亲,然后咬着嘴唇,摇了摇头。
“想象一下,”我说,“一辆有轨电车正朝五个人驶去,挽救这几个人的唯一方法,就是按下开关,让电车驶向另一条轨道,但是这样便会撞死另一个人——如果你是那个手握开关的人,你会怎么选择?”
“我——”男孩儿紧着脸,“我不知道。”
“我们拒绝做出选择,不是因为问题无解,而是因为我们不愿承认在人类的种种决定背后是冷冰的算法。”我看向妻子,“安娜,不要忘记我的一半脑子是用来干什么的——在战场上,它用一系列复杂的算法来掂量生命,而现在,就算不用什么算法我们也都心知肚明,对你和凯文来说,史蒂夫才是那个能赋予幸福更大数值的人。”
在她的眼底有泪花泛起,“肖,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我不属于这里。我要回去。”我说,“安娜,我能给你的,只有自由。”
“回去?”她疑惑地看着我,“回去哪里?”
“萨尔第维亚。”我笑了笑,“战争不是还没有结束吗?我必须回去。不是为了信仰,不是为了眷恋,而是为了自我拯救。所以——”
我来了,肖,我在你的城市。
增强视野里突然弹出的信息令我的身体僵了一下。你想干什么?
我说过,装聋作哑并不能解决问题。既然你拒绝开口,那么我只有亲自来喽。
我起身,视点在增强视野中迅速画出文字:你在哪里?我们可以谈谈,但千万不要——
一个地址链接被丢了过来。
这个地方你很熟吧?我已经到了。给你十分钟时间。
我用了整整一秒钟来思考。然后转身向餐厅门口奔去,同时用地址链接预定了一辆电动车。
“威廉!”妻子在身后喊道。
没有回头,我冲入熙熙攘攘的街道。
DAY 13
云端系统显示,这个被光秃秃的田地包围,凌乱散布着几十座颜色各异木房子的小村庄,叫作“诺夫特洛卡”,是斯图尔人聚居地。这是我们走出约根森林后设置的第一个集结点。此刻,支奴干直升机正在将断了腿的史酷比、瘪了半个身子的“剑”式机器人和几个伤重的政府军士兵吞入腹中,两架纵列螺旋桨高速旋转着,在村中的空地上搅起烟尘龙卷。
“真他妈诡异。”阿尔挤进我和尼基中间,“我敢打赌你们在这个村子里找不到一个哪怕嘴上只长出绒毛的男人。”
没人理睬他。
“喂,你们看到那几个女人的眼神了吗?”阿尔继续喋喋不休,“她们让我感觉,自己不是一个解放者,而是一个、一个——”
“一个敌人。”尼基说。
“敌人。”阿尔咽了口唾沫,“太他妈贴切了。”
——这个年轻人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在为谁而战。我摇了摇头,继续埋首于眼前的工作:自行哨戒炮、“毁灭者”全自动后勤平台和几辆REV(机器人疏散车)正陆续开进村庄。通过云端我接入REV,指挥它们对伤员进行紧急处理,随后送往最近的战地医院。而尼基和阿尔则在“毁灭者”的协助下在村外布设战术感应器和异频雷达收发器——这是联军布防的标准流程。敌人随时都可能卷土重来,届时我们需要UAV的火力支持和不掉帧的增强视野。
工作告一段落后,我们褪下外骨骼,用后勤平台上的电池组为其充电。时近黄昏,橙色的夕阳将嘴唇探向地平线,鸟儿和云朵在天空中裁下黑色的剪影。我们席地而坐,小口小口呷着战术背囊里的能量饮料,如啜饮烈酒。
悠长的沉默。
“我很好奇。”当靛青色占据大部分天幕,阿尔开口说话,“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这些人还会不会相信神灵的存在。”
我将目光投向不远处的尖顶木屋。在已然褪色的屋顶之上,金色的十字架在夕阳下氤氲着微渺的光。一个小小的教堂。
“他们——”
“他们只会更加相信。”尼基打断了我,“萨尔第人和斯图尔人是在为神灵而战,而不管结果如何,他们都会从中解读出神灵的意志。”
“为——”阿尔有些茫然,“神灵而战?”
女人和我对视一眼,似乎在犹豫着是否该将真相就这样丢给一个长不大的孩子。
我点了点头。
尼基叹了口气:
“萨尔第人和斯图尔人是这个国家里的两大主要族群,属于同一信仰的两个支系,在这片土地数百年的历史中,两个族群经常为教义阐释上的争执打得不可开交……十五年前发生了一场内战,取得胜利的是占人口大多数的萨尔第人。一俟掌管这个国家,萨尔第人政府便迫不及待地将自己对信仰的理解强加在斯图尔人的身上,他们强迫对方学习他们的经典,接受他们的教义,对不肯改宗的‘死硬分子’实施迫害——虽然迫害的具体细节被官方严密封锁,但对于那些心怀虚构正义和宏大使命感的人会犯下什么样的恶行,历史已经不厌其烦地告诉过我们……”
“萨尔第人……政府军……”男孩儿若有所思,“等等!你的意思是,我们在为那帮混蛋打仗?”
“大人物们关心的是地缘政治、战略影响力、文明与冲突,威慑与阻遏,而非善恶或者人伦这样的大词儿。”尼基将右手探入裤袋,摩挲着,“不管萨尔第人对斯图尔人做了什么,他们至少组建了一个强有力且听话的政府,可以作为山姆大叔在这片土地上的代理,实现其政治意图。所以当斯图尔人终于不堪压迫奋起反抗时,他们认为自己在进行一场圣战;但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这其实是两大国际强权在别人家里进行的一场暗中角力——你以为是谁在向武装分子提供T90坦克、S400防空导弹和电磁炸弹?”
“……操。”沉默片刻,阿尔吐出一个脏字。
“你瞧,这个世界就是这么肮脏,”尼基笑了笑,“而我们也是肮脏的一部分。”
我的心被狠狠蜇了一下。我在女人的脸上捕捉到一丝荒诞到绝望的疼痛,这疼痛伴随着星辰的微光,在她的眸子中荡漾。
“伙计们,咱们能不能阳光一点儿?”我硬生生挤出笑容,“这个世界可没有你们想的那么不堪……”
一阵嘈杂。教堂前的空地上蓦然聚起纷乱的光线。我转头,看到老人、妇女、孩子从一侧的树丛中鱼贯而出,被政府军用枪托和吆喝驱赶着,沉默而顺从地走向那个神灵的居所。尼基旋即起身,抬脚向人群走去。我将翻译贴片粘在喉结之上,跟在她身后。
“上尉,你们在干什么?”她对一个面目黧黑、军官模样的人发问,后者正喝令士兵们扳开教堂的大门。
军官转身,灯光在他眼中跃动。
这些人都是可疑的武装叛乱分子。增强视野中跳出文字。为了确保安全,我们要对他们进行集中管理。
尼基梗着脖子。你说这些老幼妇孺是叛乱分子?
军官眯起眼睛看了看我和阿尔,又看向尼基。在忽明忽暗的光线中,两个人用目光对峙着。直到确认眼前的短发女人不会退让分毫,他才开口说话:
就在刚才,我死了三十几个弟兄。那些杀人犯就是从一座又一座这样的村庄里走出去的——女士,你能告诉我,是谁将他们抚养成人,是谁向他们灌输虚伪的经典,是谁让他们的心中充满仇恨,又是谁在支持他们行杀戮之事呢?军官的嘴角卷了起来,露出森白的牙齿。在这场战争中,没有人是无辜的。
话语噎在尼基半张的嘴巴里。军官冷哼一声,慢慢转身,横着步子走向空地——在那里,政府军士兵正迫不及待地将整个村庄塞进一间小小的教堂。笑声、哭声、絮语声和咒骂声在黑夜中升腾起来,枪托毫不留情地砸向人群中不肯轻易就范的枝蔓。
此刻的情势在算法的计算范围之外,但我另一半的生物大脑却不假思索地做出了决定。我拔腿向那个军官走去,俯向他粘着血污的耳廓,翻译贴片即时传达了我的话语:
上尉,我知道你在想什么。这种木质建筑很容易失火不是吗?如果在夜里它由于某种不幸的原因燃烧起来……
军官回头。少校,我无法理解你的幽默。
这不是幽默。上尉,我严正地——
突然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儿从人群中窜出,几乎是手脚并用着奔来,巡航导弹般击中了我!我下意识地抬起手臂,将女孩儿拢住,后者抬头,眼中是一汪令人心碎的蓝。士兵们骂骂咧咧地围了上来,手中的枪乌黑森冷。
我感觉到尼基和阿尔站到了我的身后,这令我几乎瘫软的身体得到了一丝虚妄的支撑。
上尉,立刻停止你们的行动,让村民回家!我的手指死死抠住女孩儿的肩膀。
军官咧嘴。少校,我想你无权命令我。
我端起M10手枪,指向他的眉心。那这个呢?
世界瞬间失语。然后我听见枪支移动时清脆的金属撞击声,听见臂弯中的啜泣声,听见尼基和阿尔粗重的喘息。三个没穿外骨骼装甲的游骑兵和一个手无寸铁的小女孩儿被围在萨尔第士兵中间,三支手枪对十几杆步枪——好吧,我身上残存的非理性使我们这支小小的队伍再次深陷险境。
军官双手慢慢上举,嘴角仍挂着笑。好啦好啦,都是自己人,干吗要这样?听你的就是啦。大家都把枪放下——快放下!
枪口降低,翻涌的敌意却一浪一浪打在我身上。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无法忘记那种感觉:那种被无尽的黑暗和寒冷包裹,肺部被压迫着,置身深海的感觉。在深海中我保持着举枪的姿势,直到一只手挽住了我的手臂。是尼基。她将我的手一寸一寸地压低——或许被压低的,还有我的恐惧和懦弱。
这就对了。我们是友军嘛,友军怎么能拔枪相向呢?军官晃了晃拳头,将它轻轻砸在我胸口上,接着干笑两声,把头凑了过来,对着我的脸颊吐出臭烘烘的热气。少校,我欣赏你的人道主义精神,但你真的以为自己是在拯救他们吗?
我克制住呕吐的冲动。我是在拯救你。
……
“那孩子喜欢你。”尼基吐出一个烟圈,说。
我在她身边坐下。“那孩子?”
“米拉。”
米拉。那个被我“救”下的小女孩儿。政府军散去后米拉和她妈妈盛情邀请我们去家里吃饭。于是我们在那间拥挤而温暖的小木屋里享用了热腾腾的土豆烧牛肉和伏特加。吃饭时女孩儿小鸟般在我们身边盘旋,一会儿把头贴在我胳膊上,一会儿摸摸尼基的手,一会儿对阿尔吃吃地笑,一会儿又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大多数时候,我和尼基以微笑回应母女俩的热情——异国的语言会搅扰此刻的温馨,大家心照不宣。吃完饭,母女俩央我们住下,被婉言谢绝。米拉好一阵失望,但告别的时候还是在每个人脸上都轻轻啄了一个晚安。
我用手指抚摸脸颊上女孩儿吻过的地方,“她也喜欢你。”
“……真是奇怪啊,”尼基扬起脖子,目光飘向远方,“前一分钟她们把我们看作敌人。”
“我想,比起恨,人们更愿意选择去爱吧。”
她的目光下降,定定看了我一会儿。“教授,你今天真叫人刮目相看。”
耳垂发烫,我把脸扭向另一边。军用帐篷里渗出暖色的光线,阿尔的鼾声若有似无。坐在地上,湿凉的潮气正爬进身体,撩起轻微的刺痛。但我已经开始喜欢上这种感觉——和大地亲密接触的感觉。活着的感觉。也许还有在星光下和一个短发女人说话的感觉。
“你才让我感到惊讶呢。”我说。
“我?”
“你跟他们说话的时候没用翻译贴片。你懂他们的语言。”
“……忘了告诉你,我是萨尔第人。”
我凝视她的侧脸。
“在十五年前的内战中,我成了一个孤儿。是联合国难民署将我辗转营救到了大洋彼岸。在那之后的很多年里,我曾那么希望自己可以像一个普通人一样长大、读书和恋爱,希望自己可以去享受平凡而琐碎的忧愁与幸福。但我发觉自己做不到。我想,对个体而言,战争从不是单一事件,而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改变。经历过战争的人永远被战争塑造着,永远也无法摆脱战争。他们要么终日被战争的阴魂追猎,要么逼迫自己成为一个猎人——而我选择了后者。我想深入战争的血肉与骨髓之中,真正地理解战争。理解,然后克服。所以当我听到故国爆发内乱的消息时,我知道狩猎的时机到了。”尼基用力咂了口烟,烟丝热烈燃烧,发出“嗞嗞”的响声,“我回来,不是为了信仰,不是为了眷恋,而是为了自我拯救。阿尔说错了,这场战争并不是与我毫无干系——它就是我的战争。”
我迟疑了一下,“但你帮助了斯图尔人。”
尼基笑笑,“我总是一厢情愿地相信,或者说希望,这不是霍布斯那个人人与人人为敌的世界。”
沉默短暂地降临,又被远处传来的嗡嗡声刺破。一架巡逻UAV正掠过天空,它尾部的信号灯拖出长长的残影,如横向坠落的流星。
“教授,说说你吧。”半晌之后,她把脸扭向我,“你为什么来打仗?”
“……我……”
“如果不想说,你可以不说。”
“我遭遇了一场,呃,交通事故。”我绞着手指,“头部严重受伤导致语言功能丧失,四肢协调困难,记忆障碍——简而言之,我成了一个废人。你可能听说过,有一种手术可以通过植入拟态神经元来重塑受损的脑区,恢复大脑功能……不幸的是,手术的费用对我的家庭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我们根本无法承受……所以不出意外的话,我,一个曾经靠脑力谋生的人,将在福利机构机器人护工的看顾下无知无觉无忧无虑地了却下半生……”
我朝尼基伸出手。她愣了一下,随即心领神会,把烟递了过来。
“有一天,军方的人来了。他们说,可以免费为我进行手术……代价是,他们要在那部分人造脑区装入一个系统,一个可以和云端无缝链接的终端,而我必须在接下来的三年中为军队服役。——对于一个已经在心里对自己判了死刑的人来说,这是无法拒绝的价码。”烟气滚入肺中,我轻咳几声,“这就是你眼前的我:半边脑袋属于自己,半边脑袋是军方的财产,根据协议,他们有权以他们认为合理的方式使用它。就这么简单。”
“……操蛋的世界。”尼基说,“你不该被这么对待。”
“我可不会这么想。”我苦笑道,“虽然不愿意承认,但我必须要说,在重塑脑区之前,肖威廉是个彻头彻尾的混球。这个人沉浸在自己的学术追求中,对世界、对他人漠不关心——甚至包括他的妻儿……所以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儿:当一个人前额叶里的‘自我’损毁时,现代科技可以在废墟之上搭建出一个新的自我。也许是一个更好的自我。”
尼基的手搭在我的手上。微凉。一搭,一握,然后放开。她看着我,而我在她的眸子里看到了银河。
“现在的肖威廉很好,”她说,“我想,我开始慢慢地喜欢上他了。”
“我也是。”我说。
我们相视而笑。
“喂,大半夜的,你们两个不睡觉,叽叽咕咕什么?还嫌白天不够累?”阿尔在我们身后睡意朦胧地嘟哝,“……见鬼。你们见过这样的星空吗?”
我抬起头。——万千繁星,死去的抑或依然燃烧着的。流过天宇的璀璨之河。飘荡在冷寂空间中的云朵。如果不是方圆百里内的灯火被战争熄灭,我们的头顶便不会有如此美景。忽然间我有点儿好奇:那个只敬畏头顶星空和心中道德律的哲人①,会如何看待这由战争造就的纯净星空,又会如何看待三百年后依然在道德律的泥淖中挣扎的后人呢?
“……很美,”尼基的目光从我和阿尔身上扫过,“不是吗?”
我压抑着哭泣的冲动,点了点头。
DAY 234
人们消费战争,而这栋大楼就是他们大肆挥霍的地方。
警戒线。鸣响的警笛。围观的人群。新时代传媒大厦是繁华市中心里一座孤岛。
看到一楼大厅那个身上捆满C4炸药的人了吗?记者史蒂夫·雷明顿。我想你跟这个人很熟。
我从人群中退了出去。
阿尔,你想干什么?
肖,你都不知道这有多么可笑。在评论和谴责时这些人个个都是英勇的牧羊犬,可当我拿枪指着他们时,这些人却变成了羔羊。而当我向他们表明,一旦有人轻举妄动,我就会引爆雷明顿身上的炸药,这些人就更是驯顺无比了。
阿尔,你,想杀死大厅里所有的人?
在这个国家里,没有人是无辜的。增强视野里出现一个微笑的Emoji表情。是这些安坐家中的人高举双手赞成战争,也是他们一边吃爆米花一边欣赏战争真人秀;正是同样的一群人,当他们终于见识到战争的残忍与恐怖,却想通过撇清自己与战争的关系来抹掉良心上的污点——我们就是那块令他们皱起鼻子的抹布。教授,难道这些人不该死吗?
我将手探进裤袋。阿尔,你的条件是什么?
没有条件。我说过,我要把问题解决。
通过杀死这些人?
没错,这就是我的解决方案。
阿尔,我不相信你会做出这种事情。
那是你还不够了解我。教授,你难道不想知道是谁出卖了你吗?
……
是我偷偷复制了那场战斗的视频记录,把它给了你这个所谓的朋友,史蒂夫·雷明顿。而这个家伙,对,就是这个在大厅里哭得像个娘们儿似的家伙,毫不犹豫地把这段视频变成了他的独家报道,丝毫不在意这会毁掉你的人生——这栋楼里没有人在意。他们正忙着俯在战争的尸首之上,大快朵颐呢。
……为什么,要把视频给他?
那个呀。又一个微笑。因为我恨你。
那个东西在我的手掌上。银色钛合金机身。缓缓打开的黑色碳纤维机翼。电磁引擎嗡嗡鸣响。我将它抛入空中,实时画面传入我的增强视野。
教授,你知道我为什么恨你吗?
……因为尼基。
对,因为尼基。是你把她从我身边夺走。是你杀死了她。
蜻蜓大小的电磁驱动UAV飞进了大厦一楼大厅。我看到站在最前面的史蒂夫,这个魁梧的男人在瑟瑟发抖,裆部已经湿透;我看到西装革履的男男女女们,远离瘟疫般远离史蒂夫,如羔羊般挤在一起;我看到三个死去的保安,他们仰面朝天,涣散的瞳孔倒映着新时代传媒金色的徽标——振翅欲飞的和平鸽。
在二楼的敞开式走廊上,我看见了阿尔。
——手中提着微型冲锋枪,脸上挂着眼泪。
阿尔,听着,我很抱歉,但事情可以不必这样。
……在那么多个夜晚,关于我,她都对你说了什么?
阿尔,我……
教授,求你。更多的眼泪从阿尔眼中滚滚涌出。那个人已经在世界上消失了,如果我得不到她留下的“具体”,那么哪怕一点点“抽象”也好。
疼痛渗入骨髓。我闭上眼睛。
阿尔,你听我说……
DAY 145
我们在这里太久了。从伊拉克、到阿富汗、再到萨尔第维亚,我们的国家一再重蹈覆辙,以为战争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但是它并不能。当我们夺回了所有的城市和乡村,战火却依旧在萨尔第维亚内部焖烧。无休无止的自杀式袭击,无处不在的IED①,无边无际的敌意眼神。当大股反政府武装分子退入荒野和丛林之中,联军的伤亡反而激增。
我们被困在了这里。
“我们会死在这里。”阿尔说。
“请使用第一人称单数。”史酷比说。
“电子脑袋,知道你的个性为什么会被设置得这么讨人厌吗?”阿尔哼了一声,“那是因为机器人是可以随时被牺牲的,军方不希望人类对你们产生感情。所以就算哪天你被炸个稀巴烂,我们还是会开开心心地活下去。对吧,教授?”
我与尼基对视一眼,笑着摇了摇头。
自动驾驶的M-ATV全地形车正沿着约根森林边缘前进,这是云端系统指定给我们的巡逻线路。比起爆炸不断的库米扬城,这是一条相对安全的线路。但没有人敢掉以轻心。就在几天前,我们还路过了一个踩到意大利地雷的倒霉鬼——彼时他的政府军同伴正在用汤匙把他的残骸从步兵车的装甲上刮下来。
“教授,我想好了。如果能活着回去,我就去读个大学,”阿尔用眼角偷偷地瞄尼基,“兴许还可以在学校里找一个女朋友……”
尼基勾起嘴角,“那你恐怕得找个和史酷比性格差不多的。”
阿尔愣了一下,“呸!”
车厢里漾起一片哈哈声,就连挂在车后的史酷比也把它的合成笑声通过扬声器送了进来。
增强视野里出现警示信息。我的笑容冷了下来。“数据暗区!”
数据暗区。实时地图中一块癌细胞般的暗影。当标识地点的字母由黑转白,从暗影中凸显出来时,我看到尼基的腮帮倏地咬紧。
诺夫特洛卡。
M-ATV还在向前行驶。云端系统下达命令,距诺夫特洛卡最近的三个突击单元集结后前往目标地点,其他战术单元继续执行原任务。
尼基在增强视野里画出几个圈,将画面分享给我。“距离诺夫特洛卡最近的突击单元有70英里,而它还要等着与另外两个距离更远的单元汇合……肖,我们离那里只有40英里。”
“尼基,”我哑着嗓子,“我们是军人,我们必须——”
“为了报答我在世界上得到的一点点善意,”尼基的蓝眼睛直直戳向我,“我可以毫不犹豫放弃‘军人’这个身份。肖,你呢?”
沉默几秒,我把手搭在方向盘上。
“伙计们,现在由我接管载具,都坐稳咯!”
车辆猛地调头,轮胎尖声嘶叫,扫起扇形烟尘。
“教授!”阿尔在我耳边吼道,“你把我们从云端上断开了!”
“年轻人,我想你搞错了。”我咧开嘴,“在出现掉线问题时,军方的建议是投诉AT&T①。”
尼基冲我眨了眨眼,“少校,我可以理解你的幽默。”
“我不理解!”阿尔叫道,“我们会上军事法庭的!”
“只有一个人会上军事法庭。”我说,“这里应该使用第一人称单数。”
……
几根腾起的烟柱染黑了一大片天空。在肮脏的天空下我们从车内鱼贯而出,以战术队形由村庄边缘向内部接近,同时命令M-ATV做周界警戒。随着一步步深入村庄,我心中的不祥愈加浓烈:家家关门闭户。被子弹打烂的窗户和墙体。硝烟味和血腥气。地上横七竖八地倒伏着政府兵。查看过其中几个后,阿尔对我说:
“死了。不是被子弹打死的,而是——”他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刀。妈的,脑袋都要掉下来了。”
我倒吸一口冷气,踉跄着跨过尸体。用冷兵器歼灭手握突击步枪的正规军……我们即将面对的到底是什么?
“和上次一样,我的感觉很不好。”史酷比说,“不,比那还要糟。”
没有云端,没有支援UAV,没有战术中继激光防御系统——而且是孤军作战。这一次,史酷比没有被阿尔嘲讽。此刻后者正举枪前进,鼻尖渗出细密的汗珠。
他的脸渐渐被火光映红。
……燃烧的教堂。码成柴垛的尸体。暗红黏稠的溪流。这里曾经是村子信仰的中心,然而现在这里是——
“上帝不在的地方……”阿尔喃喃低语。尼基的脚步只是稍稍放缓,接着便从浓烟的穹隆中快速通过,我紧跟在她身后,“尼基,这一次我们面对的敌人……连神灵都抛弃了。”
尼基微微侧头,脚步不停,继续向西。那个方向有米拉的家。一个曾经带给我们酒精和温暖的地方。一个即使是地狱我们也要去走一遭的地方。
然后我们到了。
木屋的门敞着,屋内空无一人。在那张米拉如小鸟般围绕的木桌上,有两个盘子,盘子里是吃了一半的土豆泥和黑麦面包,有打翻的水杯,桌子旁是断腿的木椅。我和尼基分立桌子的两边,目光相接,这一次我能感觉到,如堕深海的不只我一个人。
“教授,”史酷比在门外呼叫,“收到光学感应器的位置信号……”
尼基冲了出去,“在哪儿?!”
……
诺夫特洛卡西侧。金色的麦田。未被浓烟遮蔽的蓝色天空。沿田间小路行走半分钟,我们看清了那两个高高的剪影。
十字架。也许来自教堂被拆毁的屋梁。尼基缓步驱前,将米拉和她的母亲从十字架上抱了下来。她跪在死者身旁,将她们的头发拢在耳后,为她们合上眼睛,把她们的双手叠在小腹之上……此刻的尼基是一名祭司,死亡被她整饬出一张安详的面庞。
我双手拄膝。干呕。我听见阿尔的牙齿铮铮作响,“狗娘养的……”
有数分钟之久,尼基凝视着不再欢叫与飞翔的米拉。之后,她起身,走向那个半埋在土中、有着全景摄像头的光学感应器。
“肖,”她指着感应器,“你能连上它吗?”
“应该可以,但是……”但是,这不符合信息安全操作规程。我舔了舔嘴唇,“让我来吧。”
设备初始化中,请稍候……
设备初始化成功,用户身份验证中,请稍候……
验证成功。探测到LIFI连接用户,识别号32977、32458、AI77045,是否进行视频分发?
我看了一眼尼基和阿尔,然后选择“是”。
视频被压缩。在LIFI网络中传递。解码。播放。
一片雪花。屏息等待片刻,我失去耐心拖曳进度条——没有想象中的恐怖和残忍发生。什么也没有。
“视频文件损坏,但是……”我和尼基看向彼此,“我们——”
耳罩里警报炸响。离线云端系统检测到木马入侵,立即启动了防御机制,增强视野里跳出红色警示字符:
错误304。系统锁死,30秒后重启。
出于安全考虑,被锁死的还有我们的外骨骼。还有史酷比。
25秒。
麦田里有沙沙的声音。四面八方。向我们打来的层层麦浪。劈开麦浪的黑影。
“操!”阿尔的吼叫带着哭腔,“那是什么?!”
是敌人。速度快得惊人。
20秒。
“是经过半机械化改造过的人,”尼基眯起眼睛,“是一些……孩子。”
孩子。来自这座或者那座村庄,也许嘴上才刚刚长出绒毛。他们杀了许多人,包括米拉和她的妈妈。他们把我们诱入陷阱。他们渴望杀戮,或者被杀。
15秒。
不远处传来柴油发动机的轰鸣。“是M-ATV!”阿尔叫道,如果不是被动力外骨骼紧紧箍着,我想他会蹿到半空,“快呀!打死他们,打死他们!”
没有枪声响起。
“妈的,这是怎么——”
我没法转头,但我听见了阿尔的绝望。
10秒。
根据《新日内瓦公约》,在没有人类授权的前提下,只有在敌人采取主动攻击行为时,机器人才能使用致命武器;对于一群向我们快速逼近、但没有采取攻击行为的孩子,M-ATV只能使用主动阻遏武器—— 一种令人类疼痛难忍的毫米波光束枪。
这时,M-ATV连上了我应急决策系统。攻击请求。我头颅里的军方财产立即给出建议,而我属于人类的另一半却无法做出决定。
他们还是孩子。而我还抱有最后一丝希望。
5秒。
孩子们没有被疼痛阻止。其中一个已经冲了过来。余光里,他的手臂从处于锁死状态的史酷比的下腹部掠过。下一秒,他跑到尼基面前,和她对视着。在尼基湛蓝的眼睛里,一半是仇恨,一半是悲悯。
我听到她说:“肖,不要。”
我的心被撕裂。
系统重启。
寒光一闪,长刀没入尼基的胸膛。那孩子把脸转向我,嘴角上翘,露出白色贝齿。
无声嘶吼。M-ATV对攻击行为做出回应,12.7毫米子弹把笑脸打成一团飞扬的血花。另一个孩子向我扑来,解锁的钛合金拳头向他的下颌挥去。飞溅的体液。骨骼碎裂的声音。
——爆炸。黏性炸弹在史酷比站立的地方掀起一阵钢铁暴雨。待我再次抬起头,阿尔手中的米尼米机枪已经扫倒了整片麦地。
“啊——啊——”
他的嚎叫如一枚长钉,刺进萨尔第维亚金色的秋天。
而我开始杀戮。
DAY 234
她真的这么说过?不要骗我,教授。
阿尔,我没有骗你。
片刻沉默。
教授,你知道吗,我想念你们。你们是我真正的家人。增强视野里,男孩儿的脸上浮出笑意。甚至是史酷比,我想我永远找不到和它一样讨人厌的机器人了。
我也把你当做家人,阿尔。所以不要做傻事,好吗?我知道这世界上有一个属于我们的地方,也许我们可以——
教授,我看到你了。阿尔的目光与我相对。你在那个刺客UAV里,对吗?我猜它是尼基给你的。教授,你早就可以杀了我,你在等什么?啊哈,难道我一个人的权重要超过大厅里那几十个?
在一街之遥的地方,我痛苦地摇头。
教授,我想,我并不是真的恨你。我只是……我为之前的事向你道歉。我也收回我刚才的话,这对你是不公平的。阿尔低下头。生杀予夺从来都是上帝的事情,他们不该把这个工作交给你。这一次,让我来帮你解决这个难题。
他用枪管顶住自己的下颚。
我会代你向尼基问好。
我踉跄一步,“阿尔,不!”
DAY 144
月夜。万物如披雪。那个人潜入我的营房,破开一汪粼粼波光,鱼儿一般钻进我的被窝。
“你来晚了。”我说。
尼基的额头抵着我的胸口,“阿尔非要和我聊天。”
我轻笑一声,“那孩子。”
“那孩子很单纯……也很可怜。”尼基说,“从非洲,到中东,再到这里……他经历了太多不应该经历的事情。”
“而你一直在照看着他。”
“他是我的家人。”
“那么我呢?”
尼基翻起眼睛看我,眼神清亮。“你说呢?”
有一会儿,我没有说话,只是轻抚着她因蓄长而变得柔顺的头发。
“尼基,有件事,我没对你说过。”
“嗯?”
“那场事故。”我说,“是我自己冲进了自动车道……”
“自杀?”
“我发现妻子爱上了我最好的朋友,这发现令我震惊、愤怒、屈辱,但却并不是我自杀的原因。”沉默片刻,我继续说道,“真正令我痛不欲生的是,我竟然没法否认,对于安娜来说,史蒂夫会是比我更称职的丈夫。也许也会是更称职的父亲……”
她用手指封住我的嘴唇,“嘘——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我点了点头,有液体从眼角滑落。
尼基的手从被窝里伸了出来,在我眼前打开。在她的掌心里,是一个银色的金属球。
“这是?”
“刺客UAV,电磁驱动,小巧,安静,美丽。”她说,“可以从目标的眼睛里穿入,一击毙命。”
“哇,真是振奋人心。”
“以前我替军方干过一些脏活,所以用过几次。”她用两只手指捏起金属球,借着月光,出神地打量,“有时候这东西会失灵,而在战场上,没人关心它最后去了哪儿。”
“所以你拿着的也是军方财产。”我笑着说。
“现在它是你的了。”她把金属球塞进我手里,“我想你会有办法黑进它的处理器,抹掉它的识别号,重新连接它,让它起死回生——用你更聪明的那半边脑袋。”
我用掌心感受着金属球上尼基的温热。“为什么要给我?”
“你给了我一件对你而言重要的东西,”她仰着脸,对我微笑,“所以我要回赠你一件。”
“我的,重要的东西?”
她用手指点了点我的眼角,“你的眼泪。”
“尼基,我——”
“好啦!”她用食指刮了刮我的鼻梁,“我要睡啦,还是老规矩,用中文给我念首诗。”
她侧身,倚在我的胸口,右臂环过我的肩膀。尼基说,陌生的语言会让她觉得这世界不再是必须充满意义的,会让她像小时候那样,在顿挫的美感和温暖的语调中安然入梦。
会让她相信,这世界不只是一片荒芜。
我清了清嗓子:
在赤裸的高高的草原上
我相信这一切:
我的脚,一颗牝马的心
两道犁沟,大麦和露水
在那高高的草原上,白云浮动
我相信天才,耐心和长寿
我相信有人正慢慢地艰难地爱上我
别的人不会,除非是你
我俩一见钟情
在那高高的草原上
赤裸的草原上
我相信这一切
我相信我俩一见钟情
纤细的鼾声。女人已经睡着了。我轻轻吻了吻她的额头,她的嘴角绽出了一缕笑。
尼基在睡梦中笑了。
——和所有期待着明天的人一样。
(全文完)

本文入选《归来之人:杨晚晴中短篇科幻小说集》(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最热文章

【榕哥烙科】第537期:进化的速溶咖啡,如何越来越醇?

“瓷韵中秋,科技添彩”——2024年中国科技馆陶瓷主题中秋专场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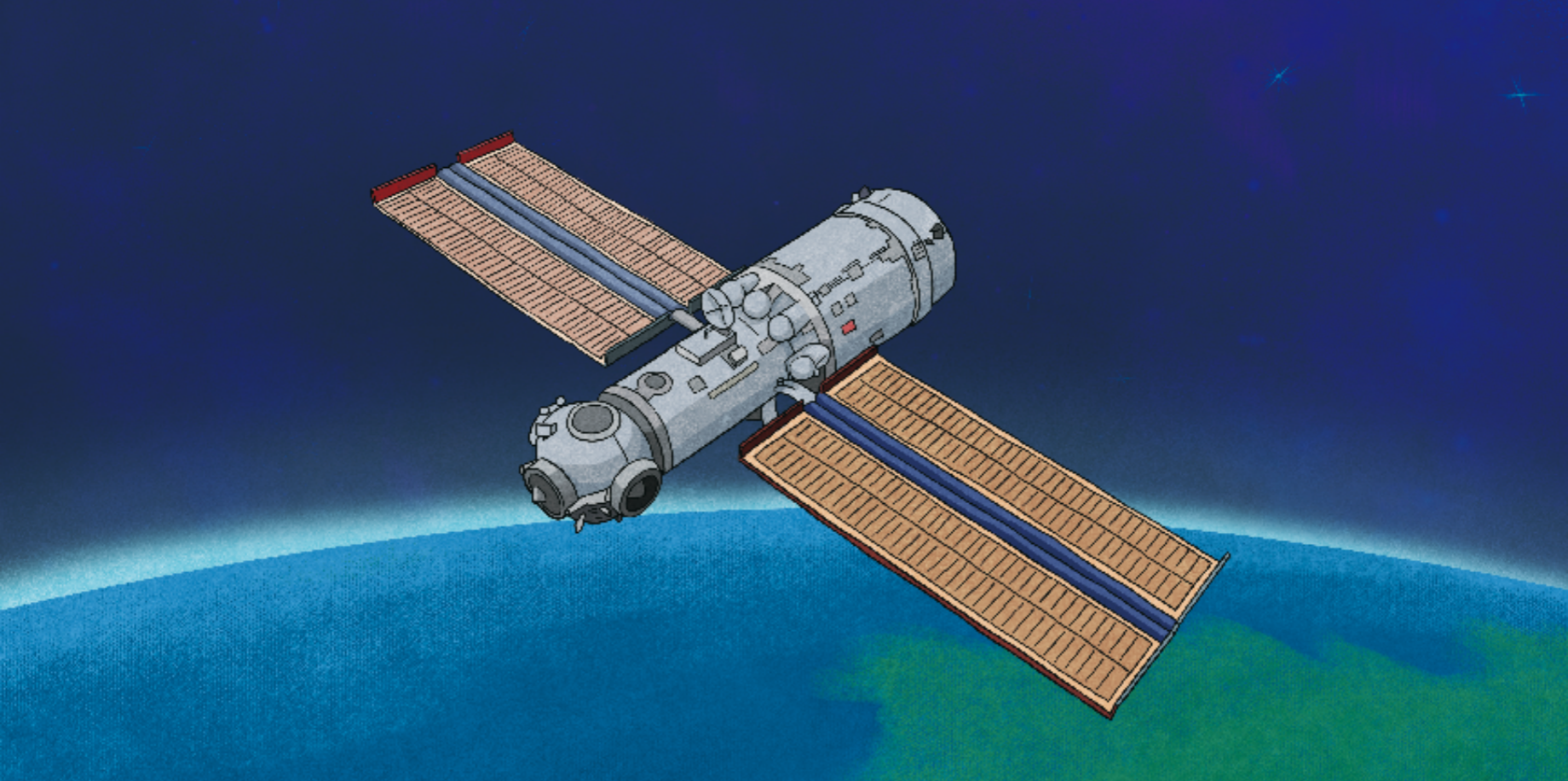
守时大神——空间冷原子钟

《爆款好人》:网红是如何吸引眼球的?

【榕哥烙科】第541期:想要一口好牙,只靠刷牙可不行

中国科学技术馆2024年体验官招募第二期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977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977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