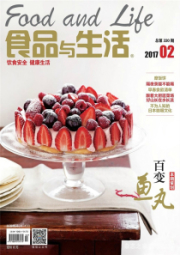放不下的那一口西点
2015-04-30 09:58:09放不下的那一口西点
█ 文_顾惟颖
上海人对西式糕点的依赖,恐怕是租界时代留下的习惯,他们一辈子都爱生煎馒头、油条糍饭,也永远离不开掼奶油、栗子蛋糕。有些人哪怕住的是蜗居斗室,也坚持拿羊角面包、牛油蛋糕当早饭的习惯,还有的人三天不碰西点就难过。美食领域的优胜劣汰有时未必可信,至少在不少人心里,多年前好些价廉物美的西点,都比现在那种高级饭店里的一道提拉米苏更美味。
解放前那些并不富裕的俄国人将他们的罗宋西菜和罗宋面包一并推及到本埠人的生活中。俄国人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上开的面包房,也是老上海们喜欢光顾的,比如著名的“老大昌”。
“老大昌”这个名字,用普通话念出来味道就完全不对,这个名称似乎只能用上海话念。念起来有一点腔调,有一点气魄,但又都是属于市井街角的。张爱玲曾经在《谈吃与画饼充饥》里描绘过“老大昌”,她经常光顾的“老大昌”在她就读的中学附近,兆丰公园对面(现中山公园一带)。那里有售一种小面包,半球型,上面略有酥皮,下面底上嵌着一半半寸宽的十字托子,这十字大概面和得较硬,里面掺了点乳酪,微咸,与不大甜的面包同吃,微妙可口。她还写到过一种肉馅煎饼,叫“匹若叽(pierogie)”,“老金黄色,疲软作布袋形。”
我倒不记得老大昌里有张爱玲所说的十字小面包与匹若叽,倒是经常看到有人排队买白脱蛋糕、朗姆蛋糕。那里还有卖一种界于冰淇淋和蛋糕之间的“冰糕”,买回家如果不吃要立刻放冰箱,否则会化掉。很多上了年纪的人看到如今价格不菲的冰淇淋蛋糕,颇不以为然:“迭格么阿拉小辰光老早吃过睐(这些我们小时候早就吃过啦)。”
另有一说,老大昌不是俄国人经营的,而是法商在1913年于原法租界创办的食品洋行。俄式也好,法式也好,一在上海生根,这面包糕点就入乡随俗,贴住本地人的口味。并且,老大昌并非上海人唯一的选择。
哈尔滨食品店是老大昌距离最近的对手,恐怕是淮海路西点店中的“头牌”,住在周边的家家户户都会去那里抢购奶油裱花蛋糕,亲朋生日送一只哈尔滨食品店的大蛋糕是很有颜面的事情。倘若想为自己买一块独享的西点,那么第一想到的就是“红宝石”的“鲜奶小方”。在红宝石面包房排队买“小方”,是这个城市30年来最执着的“甜头”。“小方”代表着一种绝对性,就是你再也吃不到比它更好吃的鲜奶蛋糕了。永远那个配方,永远简单的一小块鲜奶蛋糕上点缀一颗新鲜的樱桃,几十年都不会改变一点,却永远让人吃不厌。它的味道是清爽又回味无穷的,仿佛是素雅又布尔乔亚的少女,没有过多雕饰,却美得很高级、很天然。它是上海西点中的奥黛丽·赫本,至今没有另一款西式糕点能取代其在上海人心目中的地位。
还有一些西点,也正在渐渐流失,蛋筒、哈斗、椰丝球、蝴蝶酥、咖喱饺⋯⋯这些点心,有哪个上海人没吃过?曾几何时,那些洋行里的中国职员们,下班后买一只哈斗充饥,小心翼翼地边吃边走,尽量不让奶油弄在西装或者长衫上。那副姿态,和现在狼吞虎咽吃滚烫生煎的上班族定是不一样的。
每天要吃的点心,积攒着曾经的每一个早晨、每一个傍晚里的故事。点心,是人离不开的一种起码的生活基调,它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爱吃西点的上海人,内心免不了存有西式点心的一点锦绣与丰盛,甜的,咸的,贵的,便宜的,都依托了那一点点像模像样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