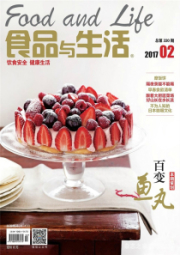腔调和味道
2014-12-30 14:45:05腔调和味道
█ 文_沸石鱼
立秋以后,骄阳日渐褪去,飘起绵延细雨。空气中吹着若有若无的风,湿热与阴冷交织,腹中饥肠辘辘,忽然就想念起最爱的点心——春卷。
一个人的口味随着年龄会有所改变, 但心中最爱依然是记忆中最深刻的那种滋味。做个不恰当的比喻:一个人心中的美食念想,犹如人生中难忘的初恋,历经多年再回想起,仿佛甜蜜如昨,心中久久有回响。吃过上海几家店的春卷,“丰裕” 的春卷个头做得大,论卖相是个大块头, 但是馅心勾芡太厚,一团糊嗒嗒;“家有好面”的黄鱼馅春卷,腥气重却没有鲜味;“王家沙”的荠菜肉丝春卷,皮太厚馅太干,没有汁水。尤其惦记“大富贵” 的马兰头春卷,皮薄而脆,娇嫩金黄, 轻咬一口清香扑鼻,豆腐干笋丝与马兰头碎末互相衬托,汁水稠浓,深得我心。
大富贵算是有些年代感的酒楼。如今的装饰还是保持着旧城厢的味道,朱漆框架的窗棂,挑高绕梁的屋顶,颀长稳扎的立柱,桌子之间的距离相隔不远也不近。周边的居民携朋友来此处喝喝茶,叙叙旧,点些小菜,悠闲话家常。我们邻桌是一对老年夫妇,男士清濯女士温婉,清粥点心几碟小菜,喁喁私语款款而谈。这一幕场景,仿佛贺友直笔下的素描画,老上海的腔调跃然纸上。
一壶清茶,一客春卷,一客芝麻苔条饼,两碗三鲜小馄饨,一份响油鳝糊, 一份熏鱼。笃悠悠的坐下,春卷蘸点米醋,小馄饨汤里的紫菜蛋皮一勺勺惊艳了人生的旧时光。窗外的雨丝淅淅沥沥, 近处的文庙、城隍庙,见证着老上海经历的雪雨风霜,沉淀了数载的物是人非, 各有其姿态腔调;但心头时不时会寻觅念想的,还是老上海的味道。那味道, 不是一种单一的表象,而是各种滋味的揉杂,是鳝糊上的胡椒粉混合着猪油香, 是熏鱼里浸透的酱油汤和冰糖汁,是老式楼宇里浓浓的家乡情,是馋时立马浮现心头的老地方。
阿奶家原先的房子是沿街门面房, 上下四大间,楼上两间住人,楼下两间开了小饭店。阿奶虽然大字不识一个, 但有魄力有胆识,深得周边邻居的信服, 颇有现今的女汉子腔调。记得小时候, 梭子蟹上市的季节,她挑选的蟹膏肥肉厚,盐、料酒、葱、姜、菱粉,不外乎就是这几样调料,但经过她的巧手调配, 几番翻炒焖煮,这梭子蟹入口鲜嫩,飘香街坊。阿奶做事利索、言语爽快,另一个拿手绝活就是煲汤。我小时候肠胃不好,她经常煮一锅猪肚肺头汤,原汤里再放入新鲜的白萝卜,大冬天里煤炉上一锅浓汤嘟嘟冒着热气,白色的汤汁赛过牛奶,稍许放点盐就吊出鲜味。时代交迭更替,阿奶已经过世二十多年了,我再没有喝到过醇鲜浓厚的猪肚肺头汤,只有在回忆中想念那汤的滋味。
老爸也许承接了阿奶的衣钵,自动升级为家里的行政总厨。读小学时,有一年中秋节老爸在家中宴客,都是上海同乡,自然爱吃白斩鸡。用散养鸡做出的白斩鸡肉质纹理清晰,入口鲜嫩有弹性,鸡皮油黄透亮又薄如蝉翼。在做调料的时候,老爸灵机一动做了改良,除了老抽、绵白糖,还加入了花椒油、碎尖椒和蒜蓉,甜中有咸还泛出浓烈的麻辣香,一扫而光便是对厨师最好的褒扬。
前几日回娘家探望父母,无意中又提及儿时的怪味白斩鸡,老爸说做菜就是当时心情的体现,一番盛情款待友人, 调料和食材的搭配完全就是凭着感觉, 把做菜当成创作艺术品,呈现出的就是一派锦泰祥和。我姑且把它归纳为当腔调和味道恰到好处的拼缝妥帖,那就是一个水到渠成。
忘记密码?
未经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复制或镜像
京ICP备11000850号 京公网安备110105007388号
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0111611号
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